原标题:《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勾画西部文学新风貌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修订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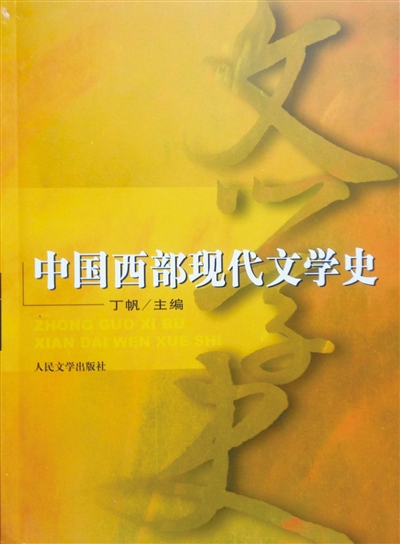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
2004年出版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西部文学史。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文学研究专家聚集兰州研讨,正对其进行修订,更名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修订后的西部文学史时段将拓展至当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飞天·大学生诗苑》、《当代文艺思潮》这两块西部文学的重要阵地就发端于兰州,一大批作家、诗人藉此走向全国,走向远方……如今,学者专家聚集于此亦富深意。
1碰撞:两地学者的共鸣
出版12年后,《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要被重新修订。
7月下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共同在兰州举办了“2016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修订会议”。《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一书的主编丁帆、副主编马永强、管卫中以及全国30多所大学和学术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50多人参加了会议。
实际上修订工作已于早前展开,还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丁帆教授牵头,联合国内20多位文学研究专家。本次修订的一个重点是将西部文学史的书写时段由“文学史”的截止时间2003年拓展至当下,同时还将对原来的部分章节做修改补充。
说起这部文学史的诞生也是富有戏剧性的。长期从事乡土文学和地域文学研究的丁帆教授,虽然很早就开始关注西部文学,但那种奇异的审美满足主要来自充满西部风情的文本和文化景观。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境遇凸显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对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学美学价值的发现,使丁帆产生了构建中国西部文学史的最初冲动。这一设想立刻得到了他的博士生马永强的呼应与赞同,生于西北长于西北的马永强虽然身处江淮、吴越文化圈,但怀想遥远的西北所形成的文化冲撞,也使他萌生了相同的想法:西部文化圈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形态,它美的价值所在和文化意义似乎被某种东西遮蔽,该是到掀掉这一“遮蔽物”的时候了。具有相同梦想的还有他们的老朋友管卫中,管卫中早年就是西部文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之一。多次学术碰撞和交流之后,孕育之中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架构呼之欲出。可以说,这部文学史的诞生与两地学者共同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有很大的关系。
“毫无疑问,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足有几百种之多,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遗憾地说,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序言中写道。
“以全新的视角打捞钩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掩埋的作家及其作品,以新的理念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从轮廓上写了一个世纪——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与此同时,它收入的作家比较全面,写作文风独特,由此,出版十余年来它不仅走进了高校,也走到了研究者案头,可以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时间的刻度里。
2凸显:西部精神风骨
那么,今天为什么要重新修订?
马永强给出的答案是:“拾遗补缺”之外,“西部风骨”的意义更加凸显。
十余年来,西部文学涌现了大量新生代作家,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多改变和突破。《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是西部文学的进行时,书写时段截止2003年,遗漏难免。所以,重新修订的内容之一就是补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现的新晋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创新与变化,以及推动西部文学发展的现代文学制度如文学期刊、社群、文学活动对西部文学的影响等。《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是文学期刊中增补内容之一,这个栏目曾刊载约1100人的2300多首诗歌,涉及30多个省市的500多所高校,包括港澳和旅美大学生。一批已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如叶延滨、徐敬亚、叶舟、于坚、王家新、海子等人都可从《大学生诗苑》寻觅到当年脱颖而出的踪迹,于坚认为:“《飞天》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马永强看来,重新修订的另一个深刻原因在于西部文学本身蕴含的深刻文化象征意味。
“作为美学精神的内化——西部风骨,已经成为西部文学、西部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大的馈赠和贡献。尤其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学热’到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一个显性与潜藏着的‘精神上的西进’,向西部寻找精神资源和动力,寻找生命的力和美,寻找诗性浪漫主义和梦想。因为西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诗成长和流传的高地,是这个文化消费时代的‘存’与‘真’。”不言而喻,在马永强眼中这些独属西部文学的东西,都在或者都会在他们的那部文学史中。
丁帆说,西部蕴藏着最丰富的文学内容,是文学的富矿。从文明史的视角看,西部文学具有“活化石”的意义。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够。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于没有外在文明的参照,创作视野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现状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造就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呼唤并期待:西部的作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智慧和恒定的价值理念创作出无愧于一个大时代的鸿篇巨制,不要忽略脚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描写的重要元素——那个能够创造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富矿——原始的、野性的自然形态和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文化形态所给予的审美观照。
甘肃“小说八骏”之一、刚刚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的作家弋舟对此做了这样的呼应,他说:“‘西部特色’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指……那些亘古与恒常的准则,永远会作用在我们的审美中”,“在主题表达中,坚持一个中国作家应有的人性价值立场是毋庸置疑的;而重要的是在题材领域里我们在多种选择中,可能自然生态的描写,风景、风情和风俗的描写应该成为我们的长项;而浪漫主义的描写方法也应该成为恢复中国现代文学此类缺失的重要元素。所有这些特质的挥发,一定会使西部文学的特征予以凸显,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新的迷人的风景线。”
3增添:三大文学思潮
这一次,以诗人阿信,作家马步升、弋舟、习习、向春、王新军为代表的一批甘肃作家被补充进入文学史。
一直以来,甘肃文学呈现的一个现象是:作家人数多,写得比较好的也多。人数多,不意味着人人皆可进入文学史。
一个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多。从十多年前编撰《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到今天重新修订,这是贯穿于编撰者内心的一个准则。
“还就有上不了(文学史)的,这里有一个‘标准’或者说‘门槛’的问题。像甘肃文坛上一位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老作家就没有进来,不是他写得少,相反他写了一大批小说,只可惜那些东西就像是一堆树叶,太轻了,没重量。”管卫中认为这一现象值得作家反思。
概括来说,《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本次修订以增加内容为主,包括两大块。一块是新世纪以来至今涌现、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及其作品,还有一块内容就是文学思潮。
言及文学思潮,于1982年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首当其冲。尽管其只存在了短短6年,但它对振兴西部文学评论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块阵地,西部文学评论界才形成了一股凝聚力,它发出的声音才获得全国学术界和读者群的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的作家、评论家也藉此被推向全国。而“西部文学”的旗号就是最早由它打出来的。也正是针对《当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力,有人发出了“中国文学评论界的重心在向西北转移”。
偶尔,马永强也会做这样一个假想:倘使这份杂志没有停刊或者多存在几年,那么中国文学的重心肯定就是今天的兰州。
历史没有假想。此次重新修订特别增加了三大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英雄主义、生态主义、神秘主义,就是由马永强负责提出并设计了写作思路的。“就东部文学现象而言,这三种文学思潮是独具西部色彩的文学思潮。”
此外,这次在原文学史1949-1979期间增加了“西部想象与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一节。“井上靖,梁羽生、金庸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几位作家都未到过西部,而西部却又成为他们的书写对象。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系列和《楼兰》系列西部小说曾在日本掀起了‘中国西部热’、‘敦煌热’,实际上他个人是1977年才来到中国的,应该看到那些历史小说是来自于他对中国西部的想象。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35部,其中天山系列有20部,而纯粹以天山为背景的有12部。金庸的小说《白马啸西风》完全发生在西部新疆,足以显示西部是他写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想象空间。”马永强解释了增加的理由。
年内,《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将正式面世。
文/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雷媛
图/受访者 马永强提供




 国学教育仅凭“热”劲还不够
国学教育仅凭“热”劲还不够
 警方侦破特大电信诈骗案
警方侦破特大电信诈骗案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美国两小熊跳入居民家饮水池沐浴嬉戏
美国两小熊跳入居民家饮水池沐浴嬉戏
 美国一对情侣海中订婚 鲨鱼做“见证人”(图)
美国一对情侣海中订婚 鲨鱼做“见证人”(图)
 刘诗诗裸妆登封面仙气十足
刘诗诗裸妆登封面仙气十足
 李光洙竟然是这样的男子 长颈鹿认真起来帅呆了
李光洙竟然是这样的男子 长颈鹿认真起来帅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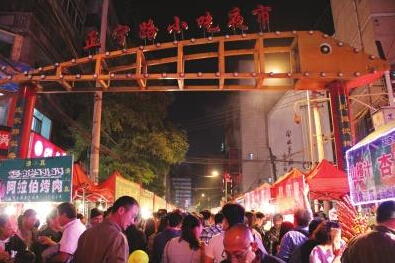 兰州将建18条夜市
兰州将建18条夜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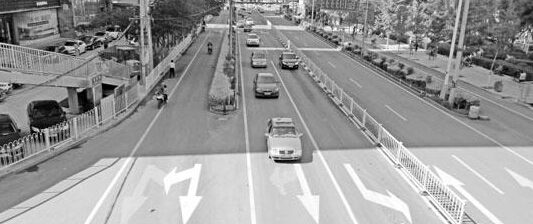 重新划线设
重新划线设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关注环湖赛:环湖军团37℃高温中征战银川绕圈赛
关注环湖赛:环湖军团37℃高温中征战银川绕圈赛
 时政要闻 省政府与国家电网公司签署农网改造合作协议
时政要闻 省政府与国家电网公司签署农网改造合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