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总结会
作者:叶舒宪
2016年7月25日下午在参观大地湾遗址之后,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团在秦安县举办总结会。会后想,更能说明问题的较全面总结,需回溯到二三十年前。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批判传统文化孕育成的“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思维偏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应只是对海开放,并强调中国文化重新向西开放的国家战略问题,即明确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构想,还大致估算出通过重开丝绸之路进行中西贸易比走海路贸易的优越性。
早在本世纪初,麦金德就从欧洲的立场出发,对东西方文化的沟通提出战略设想:中亚,包括我国新疆,蒙古一带,曾经是世界历史的枢纽地区,也将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的枢纽区,其关键是修筑一条横贯欧亚腹地的钢铁大动脉,它的机动性和效益将远远超过海洋的力量。如果说麦金德的战略设想在美苏冷战、中苏关系恶化的过去年代里有其不现实的一面,那么,在国际政治趋于缓和与互谅,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相继改善的现实条件下,从中国和世界的利益出发,提出重振丝绸之路的战略方案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了。(《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文化研究方法论》,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那时笔者在陕西师大任教,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思考,斗胆建议把重开丝绸之路作为国策:“从中国经济文化的宏观布局上看,欧亚贯通的陆路大动脉给我们输入新的血液,给全国发展的总体布局带来有益的变化,从根本上扭转重东轻西的文化偏至,实现资源、交通、人才等多重因素的优化配置与良性循环,搞活全国一盘棋,从宏观上带动地方,彻底解决中西部闭塞、贫困和落后局面,促进其经济文化的腾飞,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上书)不过,当年对重开丝绸之路给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巨大利益,还主要是从自然资源开发着眼的,如今看来显然高度不够,需要从文化资源高度重新审视问题。
二十六年过去,我们终于可以不再盲目附和西方话语,转向玉石之路即丝路中国段的实地考察。在多年的调研基础上,意识到重新面对现实、塑造本土话语的重要意义:“因为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西玉东输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资源调配之文化现象,由此便进入到玉石之路的调查课题。这才逐渐地意识到:在鸦片战争之后由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说,虽然如今已经流行于世界,却不符合国人对这条文化传播通道的认知习惯。早年我们追随西方话语提出的重开丝绸之路主张,现在看来大方向没有错,但在话语选择上却难逃西方中心的模式窠臼。近几十年来,国内的考古文博学界把这条路称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顾中西方的视角,折中一下,还是像唐代诗人常建所咏的那样(玉帛朝回望帝乡),采用先秦以来的古汉语习语‘玉帛’一词来命名,较为妥当。从跟着洋人叫丝路,到回归本土称谓叫玉路或玉帛之路,这不仅是叫猫还是叫咪的名字问题,其中隐含着从西学东渐以来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后的话语策略大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较真。”(《玉石之路踏查续记》,上海科技出版社,2016年即将出版)
2008年问世的英文书《丝绸之路史前史》一书的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认为:“旧世界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纪,这条连通中国、欧亚草原、中亚、印度、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路线,那时还延续到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甚至更远的地方。丝绸之路过去用来从中国输出丝绸,而反过来,商人从罗马和其他国家向天朝大国(中国)输入玻璃器、珠宝以及其他高艺术价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这是从国际视角对这条路的贸易情况的说明,其中并没有顾及到中国本土的视角。如果我们能够分析丝路中国段形成过程中的物质传播及其多米诺效应的因果链条,尝试论说丝路中国段的贸易整体构成;其次再从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方面的形象学角度,具体解析四类主要的传播物品的每一种,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应,就能清楚地看出对每一种西来的物质要素的神话化的文化再编码过程。我将此过程初步概括为四种主要物质的互动:即“玉、马、佛、丝”。称之为“丝路形成的多米诺效应”。
以往对丝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视角注重的是对西域的科考探险和外文语种文献的发现与解读,国内视角侧重在中西交通的历史、地理和贸易对象的认识方面。无论是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都侧重于现象层面的研究,而缺乏一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未能进入到揭示丝路文化现象所以然的理论层面,即关注和诠释如下的深度问题: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文化传播路线?在这条古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上,是什么物质要素率先登场,并发挥着依次催生或拉动其他物质要素的作用?
笔者不揣浅陋,尝试提出一种有关丝路(中国段)发生史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的理论解释,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期对新疆和田玉石的发现和持久需求,拉动中原国家与西域之间的物资贸易之路的构成,即先出现一条运送玉石的路线,从而奠定丝路中国段的早期历史(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西域和中亚的马匹大量进口(公元前10世纪——公元19世纪),更进一步拉动丝绸作为交换玉石和马匹的筹码(张骞,公元前2世纪——公元10世纪),开始陆续出口或转口贸易,并强化着这条路线上双向物资流动交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发公元一世纪前后的西佛东输的过程,特别是佛教石窟寺从喀什到于阗、龟兹(克孜尔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的。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公元三世纪后佛教石窟寺建筑与佛陀塑像的渐次向东传播,其路径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亚的路线惊人地一致。
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谓的丝路,从自西向东运输的物品看,是玉在先,马紧随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马匹之后。丝绸即帛,是作为交换玉和马的中原一方筹码,大量地和持续地自东向西运动。要追问这四种物质要素彼此之间的关联,应是一种原生和派生的逻辑关联,即因果链的关联:没有西玉东输的需求,就不会有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和骆驼伴随着玉石一起向东的旅程,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东帛西输;同样的,没有玉石东进中原的黄河河套路线,也就不会有佛教石窟寺东向传播,沿着河西走廊直到晋北的大同盆地的线路轨迹(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岗石窟)。
“多米诺”特指一种骨牌的名称,18世纪时出现在欧洲。全副牌原为28张,后发展为不限张数。把骨牌按一定距离竖立成行,只要碰倒第一张,便会一张张跟着倒下。后人把连锁反应称作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构成丝路中国段的各种物质要素而言,丝不是决定性要素,而是次生的或派生的物质。真正的原生性物质是西域的玉料。过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确认甘肃玉矿多处,即“玉出二马岗”(马鬃山和马衔山),以及渭源县碧玉乡。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武山鸳鸯玉。
没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确实材料,能说明中原与西域关联的这条路早期的物质交换情况。《穆天子传》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线问题,以及玉帛交换问题,都超出文学想象范畴,成为值得做出历史考证的真实对象。把《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团队“载玉万只”带回中原国家的行为,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有关昆仑山“多玉石”的内容对照起来看,神话历史的真实性,就显山露水了。
以上大致说明:从“重开丝路”说,到“玉帛之路”说,二十多年学术发展中的文化自觉过程。就算是总结会后的总结吧。




 省党政军“八一”军事日活动
省党政军“八一”军事日活动
 摄影大赛蒲松山参赛作品赏析
摄影大赛蒲松山参赛作品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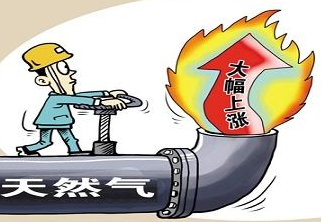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1美元在世界各国可以买到啥?
1美元在世界各国可以买到啥?
 英国大丹犬后腿直立超2米 或为世界最高狗(高清组图)
英国大丹犬后腿直立超2米 或为世界最高狗(高清组图)
 一周美图
一周美图
 关晓彤街拍玩转夏天色彩 亦童真亦优雅
关晓彤街拍玩转夏天色彩 亦童真亦优雅
 兰州将建18条夜市
兰州将建18条夜市
 重新划线设
重新划线设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文化部外联局调研文博会筹备工作
文化部外联局调研文博会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