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十四:回归篇】让流失文物“重返”家园
题记:流浪得久了,应该回家。即便回不了家,心也要回去。
很多历史上灿烂文明的城市有大量文化积淀,但实物印证稀见。
敦煌,却不同。
1900年,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藏经洞,尘封的6万卷敦煌文物问世,以珍贵实物印证着敦煌曾经的文化辉煌,也让敦煌再次成为世界焦点。
痛苦流失,敦煌文物“身首异处”。
“综合世界各地大的收藏单位情况,如果考虑到印度等国尚未完全统计到的收藏品数量的话,藏经洞出土敦煌文物总数在6万件以上。”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张元林告诉记者,这个数字虽不完全准确,但基本上反映了藏经洞文物的出土总量。而对于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称呼,国际学术界也并不完全统一。相较而言,称为“敦煌文物”(包括文献和非文献两类)涵盖比较全面和准确,其中文献部分则有兼顾其“敦煌遗留下来的这个历史性”称作“敦煌遗书”的,也有从学科角度出发称作“敦煌文书”的,也有契合专家习惯称作“敦煌写卷”的;非文献类即非文书部分,则包括绢画、纸本画、麻布画以及彩塑、木刻、壁画残块等等。“据粗略统计,目前已知英、法、俄、印等国收藏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非文献类文物当在2000件以上。”
敦煌遗书约5万多件,包括4~11世纪间800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最早的为406年(西凉建初二年),最晚的为1002年(宋咸平五年),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其中,汉文文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等。此外,还有上万卷吐蕃、回鹘、粟特、于阗、龟兹、突厥、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研究价值。
这些文献按内容来分,则包括了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宗教、军事、民族、民俗、体育、水利、语言文字、翻译、数学、曲艺、占卜等反映中古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有关的近百件,有医疗方面的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都有。
这些珍贵的文献文物,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乃至世界文明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因此,藏经洞的发现被誉为上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可惜,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也是一把双刃剑。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这些宝藏的灾难也便降临了。
自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敦煌千方百计诱骗王圆箓,用500两银子,带走1万余件稀世珍宝(其中一部分留在印度,一部分运抵英国伦敦。其中就有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之后,各国探险家纷纷来到敦煌,将大批敦煌文物珍品“瓜分”捆载而去,让珍贵文物在重见天日没多久就遭遇了“身首分离”的剧痛。
时光匆匆,这些珍贵的敦煌遗书今又安在?
“大致是国内1/3,英国1/3,印、法、俄1/3。”张元林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大的收藏单位中,分别为英国藏1.3万件,俄罗斯1万多件,印度估计也在1万件左右,法国藏6000多件,中国藏约1.6万件,“所幸这些流散国外的文物基本都保存下来了。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各个收藏单位也都在用心保存和管理这些敦煌文物。”
比如,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不仅有一个“恒温恒湿”的保管环境,而且管理和使用上也是非常严格,有专门人员进行保存、修复;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每次只能取5件,而且阅览桌上只能使用铅笔。而国内各个机构收藏的敦煌文献的保管条件也在不断改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文献的保存、修复和编目一直十分重视,将它作为善本部的“四大镇库之宝”。进入21世纪,在国家大力支持下,也修建了专门的库房,制作专柜、专盒,使馆藏敦煌遗书的保管条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精心呵护,还规定读者在调阅时必须戴手套。
藏经洞文物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令国人扼腕痛心。如何让流失文物回归故土,从此成了国人心中的一个梦想。
所幸,再纷乱的年代,总还有一些清醒的人。从敦煌文物流失海外伊始,我国学者就一直为文物回归而努力。
1909年,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经卷来到北京,向一些中国学者炫耀,令中国学者震惊不已。著名学者罗振玉得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写卷时,提请学部将敦煌经卷收归国有,使敦煌文物不再大量流散。
此后,先有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学者,编辑出版了《鸣沙石室艺术》《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等书,后有刘复、胡适等一些游学欧洲的学者怀着满腔的爱国赤诚,通过各种途径,将斯坦因、伯希和等劫走的敦煌遗书抄写或翻拍下来,再带回国内进行研究。
1934年,北京图书馆还特派王重民、向达分别到巴黎、伦敦将敦煌卷子拍成照片带回国内。他们在欧洲废寝忘食工作,带回了大量的敦煌资料。向达抄录资料达200多万字;王重民还编成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二卷。此时,古汉语专家姜亮夫也自费到英、法等地,抄回不少敦煌文献,后编成《瀛涯敦煌韵集》等书。
胡适、郑振铎、傅芸子、孙凯、陈垣等一批大师级的敦煌学学者,更是开拓了中国敦煌学的许多研究领域,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段文杰在《敦煌学回归故里》一文中说:“敦煌学是当今世界上一门显学,研究的对象,概况地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这是敦煌学的根。但在20世纪的很长时期,因复杂的社会因素,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发展比较缓慢,国际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
这极大地刺痛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成为他们发愤图强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以季羡林、段文杰等为代表的学者带动下,我国研究人员奋起直追,在文献资料不易获得的困难条件下,仍然取得辉煌成果,先后涌现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等许多敦煌学刊物,并举行了5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特别是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的召开,意味着80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此后,中国学者辛勤努力,再接再厉,使敦煌学在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和成就,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现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的中心。
“在上世纪前期,‘敦煌学’的发展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张元林说,严格来讲,“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包括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研究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看,敦煌学兴起在国外比国内要更早、规模要更大。虽然,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拿走敦煌文物毫无疑问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掠夺,但从文化的角度讲,“他们在推动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早期推动敦煌文化走向世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从学术研究的趋向上看,敦煌文物的外流还导致一个有深远影响的现象。因为敦煌,西方世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从原来只停留在完全与西方有别的儒家文化引领下的“独立的中央帝国”,开始向不断吸纳、兼容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中国”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则以石室藏书为引子,从中国对传统文化和传世文献、金石的研究,进一步向西北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更广视野拓展,并开始初步探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印度、波斯、希腊等域外文化的交流与联系。
“敦煌艺术,是外来文化特别是印度佛教文化种子,在中国汉晋以来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土壤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这是段文杰先生等前辈学者对敦煌艺术属性的精辟总结。”张元林告诉记者,尽管敦煌曾一度有过“国人伤心史”,但中国的学者从未放弃自己的“阵地”,通过学术研究等方式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就是希望即便实物回不来,也要让敦煌文物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它所具有的世界意义“魂归故里”。
身在流浪,心已先归。这,或许是敦煌文物在特定时代最好的“回归方式”。
虚拟回归,换种方式“团圆合体”。
敦煌千佛洞石室遗书,目前散存于英、法、俄、印、美、日等30多个国家。这些宝贝有没有“珠联璧合”的一天,尚不得而知。
但,希望永在。努力,也从未停歇。
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学者远涉重洋赴英、法等国,以抄录、翻拍形式,让敦煌文物回归故土,但与数以万计的流失总量相比,毕竟只是九牛一毛;后来,借助摄制成微缩胶卷和图录出版拓宽了回归之路,但难于共享。
1994年,为促进散藏于世界各地藏经洞文物的综合利用,由英国国家图书馆发起的国际性协作项目——国际敦煌项目(IDP)正式启动,目标是“使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写本、绘画、纺织品以及艺术品的信息与图像能在互联网上免费、自由地获取,并通过教育与研究项目鼓励使用者利用这些资源。”
“敦煌研究院与IDP的合作早在2003年就已起步。现在,敦煌研究院也是IDP的数据基站。”张元林告诉记者,20多年来,IDP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敦煌文献与文物的保护与共享,并在多国建立了IDP中心。如今,英、法、俄、德、日等10余个国家的敦煌文物收藏单位都加盟国际敦煌项目,成为IDP的多文种网站与数据库的主办者和资料提供者。
作为敦煌文物的故乡,敦煌研究院在与IDP积极合作的同时,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建设和虚拟回归。
2012年,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为首席专家组织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获批立项,这是国内基于敦煌文献所资助的最高级别的数字化项目。
三年后的2015年8月,敦煌研究院完成550余件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同时,与国外收藏机构陆续商谈,率先获得法国逾400G的敦煌遗书数字资料,为有计划地进行流散于国内外敦煌遗书的数字化整理和更多敦煌文物的数字回归“开了个好头”。
无论何人,身处何地,登录IDP网站(http://idp.nlc.cn),即可搜索查看已经上传至IDP的“敦煌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敦煌研究院和美国梅隆基金会的合作研究,梅隆基金会将在《敦煌电子档案》中融入世界各地珍藏的莫高窟藏经洞文物资料,其目标是“虚拟地、重新将曾经是敦煌的、而现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大量书画、文书、经卷与敦煌壁画联系在一起”,实现“将那些难以访问和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访问的内容可以被访问”的目标。
“现在是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和王道士所处那个年代已完全不同,只有加强数字化的国际合作才能彰显其活力。”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敦煌文化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人类的敦煌”仅靠一家单位是永远研究不完的,我们既不能关起门来搞学术,也不能把它藏在硬盘或是陈列馆里,而是要通过现代数字化手段与全球共享,更深入全面地保护研究。当然,IDP是机构之间的自愿合作,期望不久的将来能上升到政府主导的“国际行动”,再通过持之以恒地努力,“那么,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总有一天会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陆续‘回归’的”。
古时,因“人心相通”铸就了“人类的敦煌”;现代,同样因“人心相通”,分散存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正通过“数字化”从四面八方汇聚向一个平台,朝着“团圆合体”的梦想奋力奔跑。 本报记者 施秀萍




 【敦煌文博会】笑脸迎文博
【敦煌文博会】笑脸迎文博
 【相约敦煌】敦煌市民倾力文博
【相约敦煌】敦煌市民倾力文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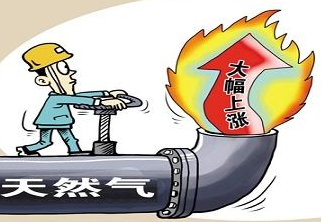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香港首家老夫子主题餐厅开业
香港首家老夫子主题餐厅开业
 癌症晚期狗狗陪主人完婚 婚礼成泪海(图)
癌症晚期狗狗陪主人完婚 婚礼成泪海(图)
 送走夏天迎来秋天杨紫粉嫩嫩献甜蜜美照
送走夏天迎来秋天杨紫粉嫩嫩献甜蜜美照
 李小璐母女美成俩小妞,这回换甜馨下巴抢镜了
李小璐母女美成俩小妞,这回换甜馨下巴抢镜了
 世界最轻婴儿诞生
世界最轻婴儿诞生
 三星遭多国封杀
三星遭多国封杀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文博会文化年展进入正式预展期
文博会文化年展进入正式预展期
 “瓷上敦煌”中国陶瓷艺术展亮相文博会
“瓷上敦煌”中国陶瓷艺术展亮相文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