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3年常书鸿等人考察莫高窟千相塔。图片摄影罗寄梅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所长来了,历史“弃儿”有了亲人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石窟保护神”。早年,出生于西子湖畔的常书鸿到法国学习油画,定居法国,事业家庭双丰收,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但,缘分似乎冥冥中由天注定。
1935年秋的一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的画册,他在著作中说:“我打开了盒装和书壳,看到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300余幅。那是我陌生的东西。序言说明这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室中拍摄来的……尤其是5世纪北魏早期的笔画,他们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甚至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但这是距今1500年的古画,这使我十分惊奇,令人不能相信!”常书鸿异常着迷,又根据卖书人提供的信息,至法国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劫去的艺术品,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辉煌的艺术宝库。
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么珍贵的艺术作品大量流失国外且在国外引起不小轰动,而国人却不自知,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为了敦煌艺术宝库,常书鸿离开生活了9年的法国,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于1936年毅然回到了祖国。
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实现梦想。1943年3月27日,他肩负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敦煌,一脚踏进千佛洞,便沉醉在浩瀚的艺术海洋,如饥似渴地临摹、研究。
1944年,常书鸿就任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与首批“莫高人”起劲地干起来。尤其是针对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制定了清理洞窟积沙、种植防沙林带、安装部分窟门、修建防护墙等一系列有效管理办法和保护措施,使石窟面貌得到初步改观。同时,有计划地对洞窟进行调查、考证和临摹,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短短一年,便临摹复制壁画上百件,整理编辑出《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上世纪40年代,莫高窟的生活条件要多艰苦就有多艰苦,常书鸿虽“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但瑰丽的莫高文化吸引着他,他和战友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然而,意想不到的事还是来了。1945年春天,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成立刚满周岁的敦煌艺术研究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残酷消息,常书鸿和战友“懵”了。
但他们舍不下令人心醉神迷的莫高窟,那里是艺术的海洋,是梦想的天堂。常书鸿决定面对现实,领导大家继续干。他用“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这样的话安慰大家,鼓励自己。又奔赴重庆,与傅斯年、徐悲鸿、向达、陈寅恪、梁思成等学者四处呼吁。
皇天不负苦心人。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段文杰、郭世清、李承仙、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等一批又一批后来成为杰出敦煌学者的年轻画家追随而来,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段欣欣向荣的日子。1948年8月28日,他们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蒋介石在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的陪同下冒雨参观;后移上海复展,两番形成轰动效应。到1949年以前,他们共临摹壁画900多幅!
冯骥才在《人类的敦煌》一书中这样描述:真正的生活总是把弱者击得粉碎,把强者百炼成钢。
科学编号,沿用至今的身份证
1949年9月28日夜,敦煌和平解放。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保护敦煌千佛洞”的命令传到了莫高窟。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胜利的喜讯传到莫高窟时,常书鸿使劲拉动了大佛殿上铁钟的撞索,让宏亮的钟声一波接一波地穿越亘古沙丘,穿越每个洞窟,直达天际。
很快,人民政府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8月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1954年,文化部特地拨款,在莫高窟第一次安装了电灯,为长期在戈壁深处工作的第一代“莫高人”送去光明;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再次对石窟进行编号。
其实,从莫高窟建窟伊始,就有编号。只不过,是按窟主家族、姓氏或窟主神氏表示,如阴家窟、文殊窟等,不具现代考察意义。
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四次,因用途而各异。
第一次,是伯希和编号。从窟区南端开始,再向两边展开,建窟时代顺序凌乱,只为配合其考察拍摄所需。第二次,是敦煌县官厅自南至北编号。第三次,是张大千编号。按洞窟下、中、上的层次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科学明了,不足之处是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附于大窟,编号比实际窟数少。第四次,是史岩编号。但只适用于准备出版的《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一书。
第五次,是敦煌文物研究所1964年的编号。基本按张大千编号,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将附于大窟的小窟、耳洞单独编号,二是将张大千“之”字型整窟反转编号。此次编号,共计492窟,一直沿用至今。




 小陇送你一场浪漫
小陇送你一场浪漫
 【首届敦煌文博会】盛会礼仪
【首届敦煌文博会】盛会礼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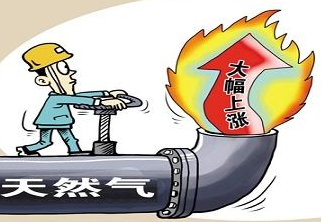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感动!美两只小狗互帮互助形影不离(组图)
感动!美两只小狗互帮互助形影不离(组图)
 全球最美婚纱照来袭 甜蜜浪漫另人叹为观止(组图)
全球最美婚纱照来袭 甜蜜浪漫另人叹为观止(组图)
 送走夏天迎来秋天杨紫粉嫩嫩献甜蜜美照
送走夏天迎来秋天杨紫粉嫩嫩献甜蜜美照
 李小璐母女美成俩小妞,这回换甜馨下巴抢镜了
李小璐母女美成俩小妞,这回换甜馨下巴抢镜了
 中国列车曼谷运行
中国列车曼谷运行
 A225“嫁入”中国
A225“嫁入”中国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敦煌文博会供电保障进入决战攻坚阶段
敦煌文博会供电保障进入决战攻坚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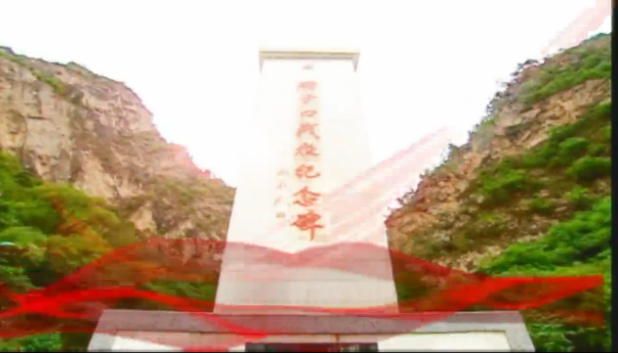 腊子口红色纪念馆
腊子口红色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