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实
阳光满山满坡都是。青草旺盛得无处宣泄,水一样流出来的绿色染遍了腊子口,染遍了甘南,染遍了岷山。
格桑花开了,比流水还快,一夜之间铺满了甘南草原,让灰塌塌、干焦的草原、高山、牛羊容光焕发。还有热情的鸟鸣,叽叽咕咕在你不远处。山里一下子欢腾起来。
直到八九月,花开了谢,谢了开,雨水连绵不断。草木让山苍茫起来、厚重起来,像一个人愈来愈浓的心思,藏也藏不住。红军就是这个时候来的,从四川若尔盖县的巴西村到甘南藏区第一个村庄干沟村。干沟村并不干,藏在大山的褶皱里,吮吸着雨水和雪水。一场轰轰烈烈的夜雨,让大山承受不住,一下子从陡峭的山上倾泻而下,达拉河水暴涨,淹没了小路、冲毁了栈道、险桥,这是山里的事,红军的事是征服山里的事情。
幽深的峡谷让大山起起伏伏,让雨水、雪水有了出路,也让人有了路。狭窄崎岖的山道把红军队伍扯成了一条山路。山大,空寂,人在这里也成了草木。
在山里,太阳跑上一天才能从一个村庄到达另一个村庄。从干沟村到俄界就是这样。
俄界,藏语“八个山头”。在这里,红军卸下翻雪山过草地的疲倦,轻轻松松地吃了顿饭,美美地睡了一觉。房子是木头做的,散发出幽幽清香的柏木和松木密密的又高又黑。远处是青稞地,抽了穗的青稞在等待成熟。村庄静静地,阳光闲散,只有“哗啦啦”的流水声在阳光里一波一波传出很远,悠远清澈。村民和牲畜都到更深的山里、林里去了。大山寂静,让人连走路的脚步也轻起来,阳光里红军忙碌的身影是安静的,走路是安静的。大山也喧嚣,雨声、风声、流水声像茫茫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大山,红军的笑声和歌声也滞留在空谷上,不肯离散。山里的时光缓慢,碎碎的有点妖娆,红军急促的脚步像飞鸟一闪而过,却是那样鲜艳的红,使人迷醉、温暖。
岗岭村、旺藏寺就在前面,全长60公里,路都在百丈悬壁上,悬空的栈道,铺板没有了,木桩没有了,鲁大昌抽走了铺板,使栈道塌陷,可是那一双双粗糙、结实的大手把铺板和木桩从几十里外传递过来,像传递火炬一样,蜿蜒、浩荡。栈道重新铺好了,悬在峭壁上的路接通了,山里的路也就好走了。一路上,鲁大昌还放冷枪,让上百名红军战士倒下,叫人多么心疼,花一样的生命啊。窄窄的几十里路红军走了两天,饿了就吃口炒青稞面,渴了就喝几口溪水。夜晚,松林里,篝火燃起来了,星星一样闪烁。山风吹过,寒凉浸透衣衫,想着旺藏寺里怒放的菊花,盛开的向阳花和牵牛花,心里就暖暖的了,多么纯粹、干净啊!他们心里暖着一团光,把受过的委屈,受过的伤害,都要忘记,不然那么长的路,二万五千里怎么走完。
山里起雾了,雨水说来就来。白龙江拒绝安静,狂风似地席卷草木和山里所有景致,尤其雨水来临,阴沉沉的更加凶猛。红军的脚步像莲花一样轻飘飘踩过白龙江,如同对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腊子口,有韭菜叶宽,窄窄的一道缝,也瘦瘦的,像刀把大山划开了一条口子,深深地,望不到底,两边光滑的岩石,齐齐矗立。草木站在高高的崖上,有些招摇,或者在半山腰枝枝蔓蔓,妩媚有些风情。随风飘逸的草木,突兀悬空起来,享受着山风带来的清爽。腊子河就在谷底,细瘦得像一根经脉,把山里的风雨雪、牛羊、鸟鸣、蓝天、人统统带到山外。也把红军带到山外。
喜欢拆桥和铺板的鲁大昌,拆了横跨在腊子河上的桥板,1米宽、30米长的桥没了铺板,像几根藤条飘在山谷。鲁大昌站在河对岸暗自窃喜。
夜晚,一山的寂静,内心如果没有盛大的淡定,罩不住这一山的空寂和灵动。黑夜里,一点点响动都会让鲁大昌紧张得用机关枪制造噪音。黑夜里,红军摸到桥上,是山风吹断了桥的横木,木头断裂的声音很清脆,也传得很远,鲁大昌的机关枪响起,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腊子河,红军像划过夜空的流星,飞向对岸。
这是1935年9月17日凌晨6时,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山里山外的路连通了。
光阴覆盖了大山,山里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都柔和的、碎碎的,开得淡雅,开得气定神闲,多像红军。




 长征会师精神报告会在会宁举行
长征会师精神报告会在会宁举行
 兰州老街为城市打造历史记忆
兰州老街为城市打造历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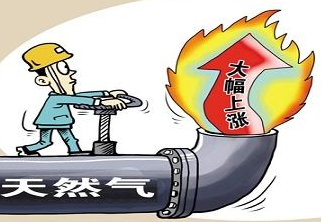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感动!美两只小狗互帮互助形影不离(组图)
感动!美两只小狗互帮互助形影不离(组图)
 全球最美婚纱照来袭 甜蜜浪漫另人叹为观止(组图)
全球最美婚纱照来袭 甜蜜浪漫另人叹为观止(组图)
 送走夏天迎来秋天杨紫粉嫩嫩献甜蜜美照
送走夏天迎来秋天杨紫粉嫩嫩献甜蜜美照
 李小璐母女美成俩小妞,这回换甜馨下巴抢镜了
李小璐母女美成俩小妞,这回换甜馨下巴抢镜了
 中国列车曼谷运行
中国列车曼谷运行
 A225“嫁入”中国
A225“嫁入”中国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敦煌文博会供电保障进入决战攻坚阶段
敦煌文博会供电保障进入决战攻坚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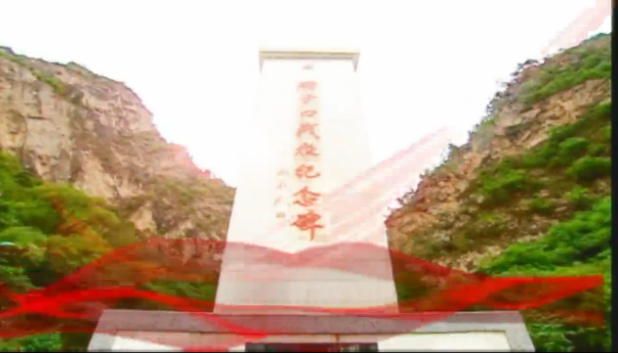 腊子口红色纪念馆
腊子口红色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