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戏剧八骏:甘肃戏剧艺术首次大集结

话剧《天下第一桥》剧照。受访者提供
甘肃首次推出的“戏剧八骏”,实则是一个“表演方阵”,“八匹骏马”——朱衡、雷通霞、边肖、张小琴、马少敏、苏凤丽、佟红梅、窦凤霞至今活跃于舞台上,而且个个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在整体上沉默、微小、喑哑的戏剧市场,这八个人的名字,至少目前在甘肃是一种标志性的“存在”。还有,这种“存在”的背后,也是甘肃的话剧、陇剧、京剧和秦腔的现实存在。
1话剧:朱衡二度“摘梅”
有一段时间了,朱衡所在的甘肃话剧院着重打“儿童剧”牌,《小猪快跑》等经典儿童剧轮番上演,“网上还有剧院售票卖得很好,场场爆满,比成人戏好多了。”朱衡说这两天他们又拍了一个美国的儿童剧,马上也要上演。
再火热,儿童剧在朱衡心中还就是话剧院谋求发展的一个“权宜之计”。在他看来,走过60多年辉煌历史的甘肃话剧院,不能没有“大戏”的支撑。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在康布尔草原上》开始,甘肃话剧院有过声名远播的辉煌,演遍大江南北,演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看过。甘肃话剧院曾是甘肃乃至西北话剧的最高水平。
朱衡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有过一次关于话剧存亡的讨论,老话剧人姚运焕说过一句“话剧死了”。2012年的《天下第一桥》成为朱衡二度“摘梅”的力作,它算是甘肃话剧院近些年来鲜有的一部“大戏”。近期,《天下第一桥》将进京参加原创剧目展演,朱衡多少有些犯愁,经历了“改制”后,参演这个剧目的一些演员退休了,难有合适的演员顶替,演员返聘必然就要发生费用,而资金缺乏一直令朱衡困顿。
从事话剧艺术40多年,时间似乎给了朱衡实话实说的资格,“不仅仅是话剧,是甘肃戏剧艺术的生存环境和土壤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了,甘肃戏剧未来的路怎么走?”现在的朱衡说得更多的是这样的话题,他觉得一个演员四五年没有一个戏,真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于这一次的“八骏”活动,朱衡觉得是对我省过去二三十年戏剧人才的一次“收割”,“收割”一词多少有点“一网打尽”的意味,“三年之后能不能‘收割’上,我不太看好。”
2陇剧:窦凤霞难忘的一盘饺子
那个场面常出现在窦凤霞的脑海中,尽管已过去30多年。
在老家宁县的打麦场上,劳作了半天的乡亲们三三两两坐下来休息,人群中突然冒出一声:“老窦,给我们唱上一段。”话音一落,苍凉的秦腔就吼了起来……
“唱的人是我的父亲窦富民。”说话的窦凤霞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陇剧传承人。
宁县是陇东的“戏窝子”,以窦富民、窦凤琴、窦凤霞为代表的窦氏家族是这里最有名的梨园世家。窦凤霞13岁从艺,23岁进入甘肃省陇剧院,她唱了十来年秦腔,并接过姐姐——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窦凤琴的接力棒,成为县剧团的台柱子。
“我学戏的时候,不知道陇剧。”窦凤霞从秦腔过渡到陇剧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到她担纲主演陇剧开山之作《枫洛池》时,已经是第四代了。多年前,窦凤霞这一版的《枫洛池》入编了“中华戏曲集锦”。去年,窦凤霞凭着“申梅版”的《枫洛池》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
七八岁时,窦凤霞就站在家里的土炕上,召集一帮同龄的小伙伴坐在地上,听她唱《红灯记》,年岁更小的时候,她就跟着四处演出的父亲,常常坐在戏箱子上等着父亲演出结束。“坐着三马子、拖拉机,在尘土飞扬中走村串乡,睡土炕、麦草堆还兴奋得很。”窦凤霞说年轻时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辛苦。
前年春天,窦凤霞随剧团到甘谷的一个镇子演出,睡的是干板床,半夜里被冻醒。寒气袭人,她再无睡意,黑暗中,窦凤霞有些“憋屈”,“(我)从省城的舞台怎么又倒回到20多年前的县剧团的状况了?四十多岁的人还在这样的环境里混?”其实,不仅甘肃,戏剧的演出市场多在广大的乡村地区。窦凤霞他们的演出多在这些地方。
第二天演完戏回到后台卸妆,有一个老乡在等窦凤霞,老乡手里端着一盘生饺子,用春天刚发出来的韭菜芽包的。到今天窦凤霞忘了饺子的味道,但还记得那位老乡的话:“窦老师,我们喜欢你的戏,你演戏辛苦,(这两天演出)吃的都是烩菜,就给你包了饺子,你赶紧煮上热热地吃上。”
窦凤霞的手机里保存着一张照片:简易的戏台上,一名女演员双手合十正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致意。照片是姐姐窦凤琴前两天在陕西一地演出结束后谢幕时抓拍的。那种情景让窦凤霞很羡慕姐姐,并给她发了一条微信:“你幸福啊!”
3京剧:马少敏移植梅派精神
马少敏正处于职业的转型期——从京剧演员到大学老师,从京剧文化的传承者到传播者。
前一段时间,她以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戏剧教研室教授的身份去中国音乐学院“充电”,主要学习了解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并录制演唱了几首新创作的京剧作品。两年前马少敏离开她心爱的舞台进入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在北京期间,每逢周末,她都会到老师梅葆玖先生家里去请教学习。几年前,她拜了梅葆玖先生为师。十多年前,二十出头的马少敏还是个“跑龙套的”,在被剧团派去北京学戏的时候,她每天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处“蹭戏”,“不管是话剧还是京剧,只要能蹭上。”那一段时光马少敏密集地看了很多部戏,她对戏如饥似渴。“看得越多,越感到自己的东西太少。”看话剧掏钱的时候多一些,马少敏记得一场戏票价10元,不过多数时候是“白看的”,因为戏园门口检票的多是她在戏校学习进修的同学。戏看多了,慢慢地也就混个脸熟,有一次去看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演出的传统京剧《穆桂英挂帅》,当时一个演女兵的演员生了急病,上不了场,紧急关头,马少敏“顶场”。
马少敏生于兰州长于兰州,小时候放学后常跑去父亲工作的东风剧场玩,就在那儿她好奇于台上的生旦净末丑,“但考上戏校前对于戏曲我就是个‘白丁’。”十来岁的时候她从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年学校录取的40人中的11名女生中的一名,进入京剧班。
马少敏记得曾经有人将她们这些在甘肃唱京剧的比喻成“沙漠里的芨芨草”,言下之意是说在没有京剧土壤的甘肃还有人坚守着,很像没有水却在沙漠中顽强生存的芨芨草。这样的赞誉让马少敏不知道该自豪呢还是悲哀?
以京剧的形式,赋予舞剧《丝路花雨》新的内容,马少敏主演京剧《丝路花雨》中的英娘,可以说是最终成就了她这个“角”的一部大戏。一直以来,马少敏的表演被认为是既继承了梅派传统程式精华,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长处,是属于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马少敏说甘肃的京剧无法与京津地区拼传统,只能拼特色和创新了。京剧《丝路花雨》一个特色是融入了大量的西部音乐。
“最重要的是京剧《丝路花雨》里有梅派的精神。”马少敏说,前辈陆淑绮老师总结说这种精神就是学戏先做人,在包容和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4秦腔:苏凤丽有一个愿景
前两天,苏凤丽被点名下了一趟乡。去的地方是临洮县,在搭建于县广场上的简易舞台上,面对着攒动的人头,她清唱了一段《三滴血》,这个是秦腔的传统剧目。
唱了这么多年秦腔,苏凤丽更多的演出机会都是在这样的乡村田野,丰富的演出经验让她知道什么样的戏是最受欢迎的。那一天,苏凤丽的大名气,还有《三滴血》这个老戏的名气,使得台下的掌声如潮水般。
如《三滴血》一样的那些传统剧目,在苏凤丽看来就是她所在甘肃省秦腔艺术剧院的“镇院之宝”,“其他曲种的剧团也是一样的,大家都会有几部保留的老剧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苏凤丽他们剧院着重对一些传统戏进行整理,按照行话说也就是“修排”。“主要是从舞美、音乐以及演员表演上进行细细打磨。”
一直以来,传统戏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观众基础,成了戏曲市场的票房保证之一。它们就是戏曲行当里的那些“拿人的戏”。
有时候,演员与名角的距离,就在于是否有一部“拿人的戏”。
五年前,苏凤丽有了一部自己的戏——秦腔版的《锁麟囊》。这是当时我省秦腔界第一次移植京剧程派的代表剧目。现在,这部戏算得上是甘肃秦腔界的一个经典剧目。后来,戏剧评论界对苏凤丽秦腔版的《锁麟囊》的肯定重点不在移植——因为早在《锁麟囊》之前已经有秦腔移植作品——而是在于它的唱腔设计和创排观念。一个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这里有秦腔经典的东西,如敏派、肖派的唱腔特点,可贵的是在原汁原味的秦中腔融入了新的东西。”相对于多少年来在戏曲界中进行的各种剑走偏锋的“戏剧革新”而言,秦腔版《锁麟囊》的成功被视为有一种借鉴意义在里面。
之后,苏凤丽的《锁麟囊》又拍成了电影,走农村院线的影片取得了据说不错的效果。
“数字电影形式对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推广非常大。”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苏凤丽在平凉老家看到了一场影响她一生的一部电影——秦腔《火焰驹》。那是苏凤丽的恩师肖玉玲的作品,肖玉玲也因为那部电影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长于偏僻之壤的苏凤丽从这部戏剧电影里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在她的脑海里第一次有了“戏”,喜欢上“戏”就是最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锁麟囊》之后的几年,苏凤丽和更多的戏剧同行经历了排戏、下乡、院团改制……5年来,她一直想着再排一出“拿人的戏”,但是她清楚也只是想想,缺好本子、缺好导演……似乎想法只能是一种愿景。现在回头看《锁麟囊》,从移植到拍成电影,苏凤丽觉得“可遇不可求”。
再过一段时间,甘肃省秦腔艺术剧院的小剧场每周末都将有演出,并已经实行了些时日,200多人的剧场基本上每场售出去的票都在百分之九十左右。“只要有好的戏,就不会没有观众,没有市场。”苏凤丽个人很不同意那些认为“戏剧已经到了边缘”的说法,她觉得,“如果没有市场,没有观众,只能说明你还是没有把事(戏)做好!”
首席记者 雷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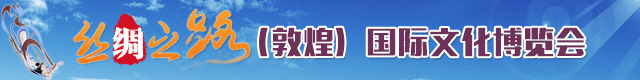



 临夏县建成布鞋加工培训基地(图)
临夏县建成布鞋加工培训基地(图)
 “活力新区”摄影大赛入选作品
“活力新区”摄影大赛入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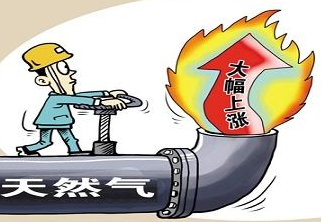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秋染
秋染
 辽宁
辽宁
 甘肃纪录片——深入现实生活 抒写时代变化
甘肃纪录片——深入现实生活 抒写时代变化
 甘肃非遗借力网游“再启航”
甘肃非遗借力网游“再启航”
 你都不知道的微信
你都不知道的微信
 刷爆朋友圈的聚会
刷爆朋友圈的聚会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短视频】挖掘民俗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短视频】挖掘民俗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短视频】甘肃省5所高校入选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
【短视频】甘肃省5所高校入选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