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梦里,她总是淡淡的一句,两句,不带任何表情。思念,穿过绵延不断的巍巍关山,牵着她,牵着母亲,牵着我。从10岁开始,母亲每年寒暑假都会带着我登上去陕西陇县的汽车,那时候的路总是坑坑洼洼,无数颠簸中,关山犹如一幅变幻多姿的水墨国画,绿意盎然,落英缤纷、层林尽染、斑驳孤寂、银装素裹……,再点上几笔或浓或淡的乡愁,如烟如雾,笼罩着张陇路,牵扯着三代人的心。
到站后,母亲唤醒我,睡眼惺忪中,母亲背着大包小包拖着我走在陇县的街道,路过那条长长的小吃街,白色的塑料大棚下,臊子面、油泼面、肉夹馍、凉拌菜……,到处飘荡的是异乡的味道,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衣襟,生怕走散在这陌生的街头。沿街走了许久,终于走上了那条羊肠小道,一路蜿蜒而上,香火味越来越清晰时,“药王洞”三个字赫然眼前。步入大门,沿山每上一段台阶后,都有一座雕栏玉砌古色古香的大殿,玉皇殿、三清殿、药王殿和土神殿依次修建,错落有致,均为仿古建筑。金黄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雕梁画栋斗拱交错,廊腰缦回色彩纷呈,每一步都是静穆与神圣。
当我们终于看见舅奶奶时,她站在清寂的山道上,素白的裹腿,青色的道衣,古老的簪子挽起高高的发髻,山风吹过,零星的几根银发拂过苍老的眼角。母亲泪眼婆娑叫了一声“娘”,舅奶奶的“三寸金莲”颤巍巍的走过来,抚摸着我毛躁的头,我害羞的低下头,偷偷打量着舅奶奶小腿上绕了一圈又一圈的白布裹腿,那些白布绕过了多少凄荒的岁月,缠过多少悲伤的过往。那是多少年前啊,似乎我还坐在舅爷的怀里拽着他一绺一绺花白的胡须,妈妈在一旁呵斥着我,舅爷一直那么笑眯眯的坐在炕上抱着我,一会摸摸我的头,一会鼓捣下炕上火盆中一个小小的砂茶罐,那清冷的早晨就在这小砂茶罐“咕咚咕咚”的声音与房后檐下一群鸽子“扑棱棱”的翅膀拍打声中消磨过了。
记忆拉长忽短,那口乌黑的棺材突兀的放在院子里的板凳上,在一片穿白戴孝的哭声中,那个在母亲故事中,年年岁岁为养家糊口从安口窑挑来缸碗瓢盆叫卖的舅爷悄无声息的走了,那些缸套缸,碗压碗的故事尘封在古老的山间小道上。母亲的故事总是交织着贫困与饥饿,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舅爷舅奶带着母亲和两个舅舅为了活命踏上了关山的道路,希冀在素有“八百里秦川”的地方有一口饭吃,舅爷担着一个小铁锅和家里仅剩的一点家舍,怀有身孕的舅奶背着二舅,拖着母亲和大舅,沿途碰到村落靠要饭施舍度日。
“关山六月犹凝霜,野老三春不见花”,那个年月冬天冰冷刺骨的关山,冷冷干枯的站在那里,一眼望不到头,舅爷用三个石头支起小锅,舅奶捏一把百家面撒在锅里搅成面糊汤,母亲和舅舅们折来路边的蒿棍做筷子,其实那清稀的面汤哪里用得到那蒿棍做的筷子,舅舅们吃不饱饿的直哭,舅爷舅奶将自己碗里的匀了又匀。大家忍受着冻僵流脓的脚的疼痛,必须赶在晚上前找一个破窑或庙来度过一夜夜的刺骨严寒。那一双双困顿机械的脚,走过饿死的尸体,趟过被抢财食惨遭杀身的肢体。六岁的母亲依稀记得在陕甘交界处,舅奶在那个冰冷刺骨的时节生下了我的小舅,逃难的路上,骨瘦如柴的舅奶没有奶水来养活我的小舅,为了小舅不被饿死,舅爷舅奶肝肠寸断,在小舅满月过三天就送给了当地的住户。小舅成年后曾几次来我家里住过些时日,他对舅爷舅奶很疏离,却喜欢呆在母亲身边,可惜那时我才两岁没有任何记忆,我思量他在养父母告诉他真相后定是难以割舍那血浓于水的亲情而不远千里寻亲,他明白当时情况的恶劣,却又难以接受亲身父母曾舍弃自己,于是在母亲身旁寻求感受深入骨髓的亲情。当小舅最后一次来家时,母亲劝说了他改掉一些懒散抽烟的习惯,敏感的小舅摔手而去,那时候没有电话手机,不识字的母亲也不知道小舅的通信地址,至此了无音讯。有时候我会想会不会有一天小舅或者小舅的后人能看到这篇文章,小舅有一天会再次回来。
关山的冷厉渐渐消逝在身后时,开春时节舅爷舅奶带着母亲和舅舅们终于走到了陕西省千阳县,母亲说他们在一个叫“高崖公社”的地方住了五年才返回张棉驿。我查询着母亲口述中的千阳县高崖公社:“千阳县隶属陕西省宝鸡市,位于陕西省西部。北靠甘肃省灵台县,南邻陈仓区,东与麟游、凤翔县毗邻,西同陇县接壤。千阳县辖6个镇、5个乡,98个行政村:城关镇、崔家头镇、南寨镇、张家塬镇、水沟镇、草碧镇、沙家坳乡、文家坡乡、柿沟乡、寇家河乡、高崖乡。高崖镇地处陕甘两省交界的北部深山区,距县城62公里。东与麟游县毗邻,北与甘肃省灵台县接壤,千高公路穿境而过,通达两省三县,是陕西省通往甘肃的重要驿站,素有‘二牛耕地跨两省,鸡鸣一声闻三县’的美称” ,一张平面的地图面前,我看着起点“张棉驿”,找着终点“千阳县高崖镇”,思索着那艰辛冷酷的岁月中那条在山峦重叠,溪壑密布中蜿蜒而去血泪斑斑的路。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在千阳县高崖镇生活了五年后,家乡情况好转后,舅爷舅奶商量后举家回迁,清扫完荒芜的院落,开始新的生活。舅爷在世时,大舅结婚后分家住在村子的另一头,二舅一家和舅爷舅奶同住,舅爷去世后时间不长,二舅就把舅妈和儿女接去了靖远煤矿,剩下舅奶奶一个人在偌大的院子里,早出晚归干着农活。母亲每年农忙季节匆匆忙忙把家里的农活干结束,就带着我去舅奶那里帮忙,沉甸甸的麦垛像一座大山压的舅奶喘不过气,粗粗的麻绳磨着母亲单薄的肩膀上的茧子。
日月轮转,舅奶和舅爷忍饥挨饿拼死拼活带大的娃儿们啊,岁月的年轮变幻了一切,曾经稚嫩的小脸有天就成了憎恶嫌弃的白眼,喊爹叫娘的童声有天就成了呼天喝地的斥责。我始终记得有次去舅奶家,大舅和舅妈干完活在舅奶那里吃饭,舅奶和妈妈谦卑的把饭碗端上炕桌,小小的我看着大舅坐在炕上抬头低头间对舅奶的厌弃与白眼,那个表情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这么多年。每年庄稼收割到场院,碾好簸干净后都放在大舅家,舅奶一个人吃完最后一把面最后一个洋芋后,提着那个破旧的篮子去大舅家去要,大舅瞪着眼一声不响窝在炕头抽着旱烟,舅妈黑着脸骂骂咧咧不愿给。每年到舅奶家听她诉说着,舅奶和妈妈相对抹泪,那时的我心里沉沉的,后来懂得那是忧伤。当舅奶在大门上挂上那把锈迹斑斑锁子时,我不知道她熬过了多少个绝望心伤的不眠夜;当舅奶离开村口时,我不知道她抹过多少次眼泪;当舅奶踏上去陇县的汽车时,我不知道她的小脚是否有过一丝迟疑与留恋。后来在母亲知道舅奶去了陇县时,她流了多少泪再也劝不回留在“药王洞”的舅奶。
于是,母亲带我寒暑假去张棉驿石峡口的路换成了去陇县的路。“衔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关山,关山,承载了千百年来多少人的离愁和乡思。年少的我一会儿在舅奶的诵经声中昏昏欲睡,一会儿在舅奶让我教她经文中艰涩难懂的繁体字时偷溜到后山打着不知名的野山枣。空寂的后山,夏季时漫山遍野是郁郁葱葱化不开的浓绿。冬季时沟边几棵高大忧伤的柿子树上落寞的挂着零星的红柿子,可望而不可及。我转悠在这个空旷的道场,寒暑更替,年复一年,舅奶折子一般的经书诵读了一本又一本,我在磬声诵经声中听着善恶因缘果报的故事,小小的黄毛丫头也成了安静的女子,我只愿这安静平和的日子一直这么走下去。
离殇总是刹那间,2004年冬天,我正值高三,母亲接到药王洞打来的电话就急匆匆赶往陇县,舅奶蜷缩在炕上,干枯瘦弱的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熬完最后的时日,舅奶永远留在了陇县北千山。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十年光阴,我定是负了你,我不知道你坟头的草有多长,我不知道后山的野枣子是否落了一地绯红,我不知道那高高的树顶是否还挂有柿子;十年光阴,我定是负了你,你曾诵读的经书被岁月尘封在了何处,你游离在我的梦里只是淡然的远望,烟雾氤氲的关山渡口你是否找到了回家的路。寒月离歌,前尘后世关山魂;山迢路漫,望断天涯何处诉衷肠;路人笑愚太痴狂,泪眼婆娑酒一杯,醉笑陪君三万场,只为离殇。
作者 王志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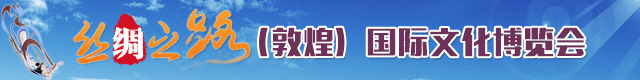



 临夏县建成布鞋加工培训基地(图)
临夏县建成布鞋加工培训基地(图)
 “活力新区”摄影大赛入选作品
“活力新区”摄影大赛入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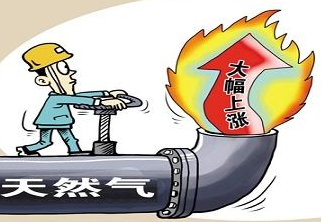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山东
山东
 湖南
湖南
 甘肃纪录片——深入现实生活 抒写时代变化
甘肃纪录片——深入现实生活 抒写时代变化
 甘肃非遗借力网游“再启航”
甘肃非遗借力网游“再启航”
 你都不知道的微信
你都不知道的微信
 刷爆朋友圈的聚会
刷爆朋友圈的聚会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短视频】挖掘民俗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短视频】挖掘民俗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短视频】甘肃省5所高校入选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
【短视频】甘肃省5所高校入选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