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边说着,刘劲勋打开了他的笔记本电脑,与记者交流起了他不同时期的作品。《苏菲的高原》是他较早期的一组经典视觉作品,这些照片主要拍摄于宁夏西海固地区。“90年代初,我看了作家张承志的穆斯林宗教题材小说《心灵史》,书中对于回民的精神格局的描写,给了我强烈的启发,而且我是个在城市中长大的穆斯林,我想要通过这组作品找到一种归宿感。但是当时我在外地没有精力去拍,于是这个念头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埋藏在我的心里,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芽。90年代末我回到兰州后,就慢慢为这个主题做一些视觉上的储备,再后来,在一个穆斯林摄影家的启发之下,我终于下决心去拍了,这组作品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按《心灵史》这本书的文本按“文”索骥,去寻找我想象中的画面。拍摄过程整体上来说是很顺利的,大部分拍摄对象都很配合,但是也有碰到过很难沟通的情况,尤其是比较封闭的地方就更加难上加难。遇到极端的情况时,相机都被别人拿走过……”说到这时,他豁然地哈哈大笑。

他方
《他方》也是刘劲勋的代表性作品。“我12岁随父亲去藏区拍照片,长大以后我想通过自己的照片找回我的记忆。当时拍摄这组照片时,我刻意用了最便宜的LOMO相机,胶片用的是过期30年的老胶片,最后出片的效果让我惊艳。”作品中那些粗糙的颗粒和肌理形成了特别的感觉,那些混沌的纹理,模糊的质感,如梦似幻。据刘劲勋说,由于拍摄时正在刮沙尘暴,很多沙子钻进了相机,在胶片上形成了一道一道的刮痕,这些都为这组照片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回顾之前的作品,他说,以前我会刻意追求美学的视觉表达,而最近几年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就像我最近的作品《该隐》,这是一种带有人的原罪拷问的作品,是我和我父亲的作品的合集。我想表达一种对自觉者和背叛者的思考。当然我的作品也可以重新解读,我觉得欣赏作品就要善于拆解,学会拆解和平时的知识积累息息相关,如果缺乏一定的积累,领悟与觉悟能力就不够,是拍不出好照片的。

《匈奴的名字》也是刘劲勋比较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这组照片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影像。他在评价这套作品时说,我现在做摄影喜欢用“消解”这个概念,或者可以说是摄影上的“减法”。匈奴在历史上是独立的民族,而现在仅仅留下了“匈奴”这个名字而已,因为匈奴的历史都是它的敌人和对手书写的,正因为我们无法去准确定义它,所以会对其充满想象,可以发挥的空间也更大,所以我想通过这个作品,把既有的摄影概念消解掉,让摄影回归到本身,还原本真。

记者看到这组作品中有一扇铁质的栅栏,于是问到他这个冰冷的栅栏与匈奴有什么关系。刘劲勋说“一般来讲,我喜欢拍我看不懂的东西,首先,拍这张照片时我并没有强烈的意图,图片表达需要借助想象,这个栅栏有着严酷的颜色,阳光下闪着寒光。有一种强烈的张力,我的照片中一个具象的匈奴都没有,但是每一张都组合起来之后让人觉得就是匈奴。

苏菲的高原
与其说是交谈摄影艺术,不如说是在交谈哲学,他说,摄影就是个矛盾统一体。“摄影对我来说,现在已经不仅是一幅图片,我觉得它更是一种想象,是一种可能性,最终成形的作品只能无限接近,但是不可能实现。学任何一门知识到最后都应该要达到通达的境界,否则就是被方法和工具绑住的人。”他坦言:“我现在的摄影理念,能读懂或看懂的人确实不多,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要追求我想要的艺术表达。”“摄影是既有物,我只是在搬动它而已,或者说,我只是起到发现了它,并没有带着主观刻意,也不想给它赋予特定的意义,就像麦田不意味着丰收,现在在我看来,麦田就是麦田,其他什么都不代表。所谓大美无形,最重要是思考的过程和拍的过程。”

匈奴的名字
“我想摄影的美学可能跟人的本能有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代艺术出现后,认为美学其实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色即是空。”刘劲勋这样认为,作为东方人,摄影师应该要诉求东方的艺术精髓,摄影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东方哲学,甚至也可以将摄影、建筑、哲学、美学从同一个角度去理解,看得多了就会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点。这些年,刘劲勋偏爱去中亚的一些国家采风,每次他像独行侠一样只身一人踏上陌生的土地,“我喜欢异域的地貌、气候、人文、饮食给我带来的碰撞。摄影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去不同的地方,接触不同的人,并且用心体会他们……”
记者 华静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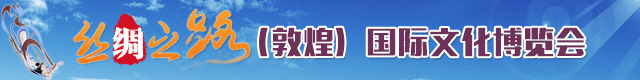



 临夏县建成布鞋加工培训基地(图)
临夏县建成布鞋加工培训基地(图)
 “活力新区”摄影大赛入选作品
“活力新区”摄影大赛入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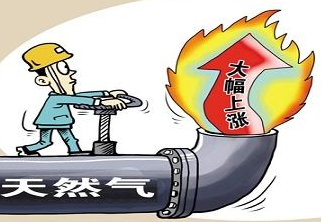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春色
春色
 成都
成都
 甘肃纪录片——深入现实生活 抒写时代变化
甘肃纪录片——深入现实生活 抒写时代变化
 甘肃非遗借力网游“再启航”
甘肃非遗借力网游“再启航”
 你都不知道的微信
你都不知道的微信
 刷爆朋友圈的聚会
刷爆朋友圈的聚会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短视频】挖掘民俗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短视频】挖掘民俗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短视频】甘肃省5所高校入选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
【短视频】甘肃省5所高校入选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