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内的一座古戏台新华网发
“设瓮助声”是指古代在戏台中设置陶瓮以扩声传声的方法。此法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认同度,然而近当代以来却备受争议。其论争焦点为是否存在“设瓮”实例遗存或相关实物及其有无作用,其论争的问题主要有两层,一是是否存在设瓮史实?二是如有设瓮史实,陶瓮如何置放?是否可以助声?
“设瓮助声”的源流
设瓮助声技术,源于战国时期墨子设瓮以防挖地道偷袭的守城技术,一直流传到清代。战国时期《墨子》载:“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顺之以薄鞈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之穴之所在。凿穴迎之。……杀,俚两罂,深平城,置板其上,板以井听。……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埋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唐代李筌著《太白阴经》载:“选少睡者,令枕空胡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有响见于胡中,名曰:地听”。唐代杜佑著《通典·兵五》载:“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甖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称其为“瓮听”或“地听”:“右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中,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右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熏灼法。”清官修史料《清实录》(咸丰朝)载:“该督抚等,务与声势联络。以期彼此策应。遏贼登陆之路。又有人奏、务防地雷穵濠瓮听之法。一并抄给阅看。……所有城内布置机宜。与瓮听诸法。须严密防备。不可稍涉疏忽。”光绪年间,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中也记载了“设瓮”守城的方法:“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绕城多坎,伏瓮而听,其声空空,掘堑以迎。……设瓮听贼临城下,须绕城多掘坑,内安大瓮,使人坐其旁听之,瞽者亦可用。如贼击地道,必有声息。”
汉以降,设瓮技术始用于古琴扩声。西汉司马相如将瓮埋于琴台下以使琴声加大。此事被明代张岱在其著作《夜航船》(卷九)之《礼乐部·乐律》中记述:“相如琴台:司马相如有琴台,在浣溪正路金花寺北,魏伐蜀,于此下营掘堑,得大瓮二十余口,以响琴也”。明代屠隆《考槃余事》卷二载:“琴室,宜实不宜虚,……如平屋中,则于地下埋一大缸,缸中置一铜钟,上用板铺,亦可”。
古戏台建筑中“设瓮助声”,可能因其司空见惯,或因其为民间技术不值一提,在古代文献中难觅其踪。但作为建造之初即以演戏为目的的古戏台建筑,古人对其助声功能的期许在碑刻中隐约可窥。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苗匠村土地庙康熙八年《苗匠村重修社庙创建舞楼碑记》载:“舞楼立而灵鼓彻云,耳房具而骏奔下榻”。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同治五年《重修戏台窑亭记》碑载:“第昔之戏台规模卑狭,墙垣壅蔽,不足以壮观瞻,不足以舒耳目……”。在其他古建筑中,虽无“设瓮助声”实例,但有利用其他空腔扩声的实例,如山西普救寺莺莺塔的空腔声学效应早在明代就已广为流传。
论争的缘起
当代学界,中科院马大猷院士1979年在其论文《中国声学三十年》中首肯“设瓮助声”方法,谈及“用陶瓮在舞台下或墙壁上做共鸣器以扩大声音或对声音的吸收,则是历代常用的音质控制技术”;中科院戴念祖研究员1992年在其《中国声学史》一书中也肯定此法,并对其历史源流进行了系统梳理;马大猷院士2004年又在其著作《现代声学理论基础》的6.3.1节论述亥姆霍兹共鸣器时写道:“亥姆霍兹共鸣器可受外面声场的激发并消耗其能量,但空腔内的振动又可通过短管辐射声波加强外面的声场,中国和欧洲古代都有在戏院埋藏空罐以加强歌唱效果的事。在《墨子》一书中还载有用地下埋藏的大瓮放大敌军活动的声音的设备(在抗日战争中在地道中也用过)。”据说山西部分古戏台的台基下都埋有助声大瓮,北京恭亲王府、陕西米脂闯王行宫、山西晋祠等景点的解说词中对此也都有介绍。
2004年,“设瓮助声”技术受到学界质疑。同济大学王季卿教授在其论文《析古戏台下设瓮助声之谜》中指出,台下设瓮为以讹传讹,并引述多家著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论争由此开始。由于一直没有发现设瓮实例或相关实物,“设瓮助声”之“史实”始终未被证实,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或“虚构的事实”,学界因而论争不已。
这场论争的主要观点有二:一持肯定观点,认为古戏台扩声技术中肯定运用了可扩声的陶瓮,代表人物为中科院马大猷院士。一持否定观点,认为古戏台下“设瓮”为以讹传讹,并无相关实例。即使“台下设瓮”,由于其上“铺砖覆土”,声不能透,况且陶瓮能共振的频带极窄,因此并无效果,代表人物为同济大学王季卿教授。这场论争的范围还涉及国外的此类现象,如有人将其与古希腊剧场之设瓮技术进行了比较。
论争的解决
在中路梆子戏盛行的晋中地区,笔者经过大量调研,于2013年5月在汾阳市石塔村龙天庙发现了曾对称嵌设在戏台两侧山墙上的十四个腔大口小的陶瓮,据庙中残碑所载文字显示嵌设陶瓮的时间下限应不晚于咸丰年间。这为“设瓮助声”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在考察现场,笔者发现原戏台已被拆除,现在旧址上新建了四大天王庙。据文物部门提供的老照片得知,十四个陶瓮,每边山墙各对称卧嵌七个。七个陶瓮的容积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大小各一,中等的五个。它们瓮口朝外,口口相对,嵌设高度均约1.5米。与民间传闻和已掌握的文献相比,龙天庙古戏台陶瓮嵌设方式的特点有二,一为陶瓮嵌设位置已从台基底下转变为前台两侧山墙1.5米高处;二为陶瓮的容积大小不一,有三种规格。经声学仪器的测量结果分析,发现陶瓮的固有频率(即共振频率)明显可将声音放大,其对应音高为D、F和G三音,而这三音恰恰是曾盛行于汾阳一带的G徵调式的蒲州梆子戏的调式主音、闰音(特色音级)和宫音。特别是14个声瓮口口相对,对称卧砌于前台两侧山墙,瓮口高度约1.5米,与演员口腔高度接近,便于演唱声直射入声瓮,放大后的声能也便于传出。由此,龙天庙陶瓮可否扩声不言自明。
此外,笔者还在汾阳周边地区发现了一座台面铺设0.05米厚木板,台下设长8.83米、宽5.35米、深0.84—0.92米密闭空腔以置放扩声陶瓮的平遥县孟山乡照四角村双神庙古戏台遗存和两百座后台设窑洞(窑洞为共振空腔)的古戏台遗存。“台下空腔”内设的陶瓮、后台所设的窑洞和墙上设的陶瓮其声学本质都是空腔共振。瓮置“台下空腔”中,“腔口”覆板。若上覆薄板,则声或许可透,会有一些扩声效果;若上覆厚板或板上再铺厚砖,则声不易穿透,其效果甚微或几无效果。可能由于上覆薄板受力不足,致使瓮上改铺厚板或将瓮置于厚砖砌筑的洞中,致其助声效果甚微。这或许是“台下设瓮”向“台(墙)上设瓮”或“后台设洞”发生转变的原因。对部分后台设窑洞的古戏台实测结果也可证实其共振扩声性能。可见,汾阳龙天庙出现陶瓮共振扩声技术并非偶然。
事实上,瓮的形状对其声学性能也影响较大。无论战国时期可容三十斗以上的“罂”、汉代大瓮、唐代的“空胡”,还是明代可置放铜钟之“大缸”,皆应为肚大口大之容器,其形状同今用柱形敞口水缸。龙天庙声瓮腔大口小,较敞口水缸的声学性能有很大飞跃,为典型的亥姆霍兹共鸣器。从声学原理上讲,敞口容器的声学性能以交相反射为主(若振动信号来自腔壁,由于腔内空气的密度远低于容器腔壁,故腔内空气可增大其振幅,但非共振);腔大口小容器,不仅可对大多数声波交相反射,而且还可对与其固有频率相同的声波产生共振。换言之,龙天庙声瓮是设瓮助声技术从交相反射扩声升级为共振扩声的反映。从国际学界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看,丹麦BK声学公司创始人Jens Holger Rindel于2011年研究古希腊剧场观众席下所设声瓮,综合分析其声瓮形状和置放方式,认为其几无效果。相比而言,山西龙天庙的设瓮技术和效果或许超出了古希腊剧场。这些古戏台声学既体现了我国古人对声音的认知和应用水平,也是我国古代在戏剧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




 甘肃省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综述
甘肃省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综述
 兴隆山举行公祭烈士活动
兴隆山举行公祭烈士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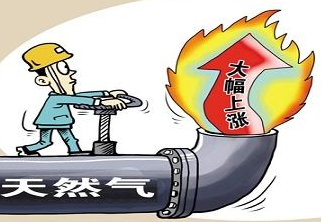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千钧一发!瑞士“钢丝侠”42秒跑100米(组图)
千钧一发!瑞士“钢丝侠”42秒跑100米(组图)
 澳大利亚沙漠灯光展 万“花”齐放(组图)
澳大利亚沙漠灯光展 万“花”齐放(组图)
 莫文蔚期待与李宗盛再合作 因缘分献声《美人鱼》
莫文蔚期待与李宗盛再合作 因缘分献声《美人鱼》
 小李子"夺奥路"敌影重重 万磁王、德普船长都是劲敌
小李子"夺奥路"敌影重重 万磁王、德普船长都是劲敌
 影星黄渤临洮祭祖
影星黄渤临洮祭祖
 乌克兰导弹馆抢眼
乌克兰导弹馆抢眼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清明春雨思故人 缅怀英烈在心头
清明春雨思故人 缅怀英烈在心头
 广河:电商小平台 扶贫生力军
广河:电商小平台 扶贫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