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生态中国频道: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城南,在绿树环抱的陵园中,有两座并排的陵墓,艾黎、何克的名字镶刻在黑色大理石墓碑上。他们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救助并抚育我成长的异国养父。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乔治·何克是英国人。日本鬼子的侵略战争,摧毁了我的家,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正是他们的救助和抚养,才使我得以生存下来,并且长大成人,三个国家一家人的特殊家庭,所谱写的动人故事,闪耀着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将为世人所铭记。
搞工合运动甘做“中国头号白人苦力”
1927年4月,路易·艾黎从新西兰来到中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0年。这期间,他先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督察,两年后,担任工厂安全督察长。1932年,在上海的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介绍艾黎与宋庆龄相识。在宋庆龄的倡导下,艾黎组建了外国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史沫特莱、斯诺、马海德等。通过学习,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实践中,并且成为人所共知的著名国际友人。
开展工业合作运动,支援抗日斗争,是艾黎抗日活动的大手笔。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工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工人失业,流离失所。当时全国工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沪宁杭地区,一旦被敌人占领,中国的抗战就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因此,转移、疏散工厂,组建新的适应战时的工业合作社,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在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为行政院负责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艾黎组织把武汉64家企业搬到了宝鸡。由于毗邻西安、延安,西迁到这里的企业能够重新复工生产,不仅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工业设施,还安置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些企业所生产的棉纱、棉布、军毯在支援抗战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工合成立后,相继在洛阳、宝鸡、成都、赣州建立了办事处,分别负责中原、西北、西南、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的组建和运行。合作社的口号是“努力干、一起干”。兴办的小厂有机械、化工、面粉、造纸、纺织、被服、印刷、炼铁等等。由于它的规模不大,技术含量相对不高,投资小,见效快的特点,便于避开敌人的轰炸而免遭破坏,很适合于隐蔽、转移。它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品种繁多,涵盖民用军需的许多方面。工合事业由于适应战时需要,最初得以迅速发展。到1940年10月,短短两年时间,已在全国16个省,建立了2400多个各类合作社。从业人口约2万人。
艾黎曾三次到延安访问,工合事业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欢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地区,建立各种合作社。这样,工合就成了既能够在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又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存在和发展的组织,十分有利于坚持全面抗战。在当时通信、交通设施都很落后的情况下,艾黎跑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行程2.4万多公里,乘火车,搭汽车,骑马,许多时候还只能骑自行车。他不畏艰险,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无数的困难才清楚地了解到各地的真实、具体的情况,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物资调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埃德加·斯诺早在1941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登载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这篇文章介绍了艾黎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意义,赞扬了艾黎不辞劳苦,排除万难,支持抗战的坚强毅力,肯定了艾黎自己甘做“中国的头号白人苦力”的精神。
创办学校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
工合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国民党官僚的一块心病。艾黎于1942年被撤销行政院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被赶出了工合总部。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在被撤销职务后,他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方面。创办培黎学校,培养人才,是他在抗战后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壮举,为世人所称颂。前几年上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的部分情节,就取材于这所学校。
1942年,艾黎把任西北工合秘书的英国人乔治·何克,调到位于秦岭南部的小镇双石铺,担任培黎学校的校长。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于牛津大学毕业,同年来到中国。先在上海,后去延安、武汉。他目睹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实在忍无可忍,决心留在中国,揭露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侵略事实,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何克到任培黎学校校长后,陆续招收了60余名贫苦和战争难民子弟入学,他利用嘉陵江的水作动力,兴修纺织厂、机械厂,亲自带领学生、工人一起干,丝毫没有英国绅士的影子!到1944年,学校初具规模,逐步完善了半工半读的教学秩序。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校内常常传出欢乐、雄壮的抗日歌曲,学校办得生机勃勃。
收养孤儿细心关爱但从不娇惯
1941年春,在宝鸡西北工合内部,掀起了一股排挤、打击、迫害正直的进步人士的逆流,搜查缉捕共产党员,是他们最阴险、最毒辣的阴谋。我的父亲聂长林当时也在宝鸡工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组织上得知他已经列上被缉捕名单时,立即决定调他离开宝鸡,先去中条山木炭合作社暂时躲避,等待时机途经洛阳,再去晋东南。因此,我的父亲连夜离家出走,根本顾不了安置家里的一切。三个月后,他在洛阳等待过河证件,准备渡过黄河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时,遇到从那里刚刚回来不久的何克。何克答应关照父亲一家:四个年幼男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回到宝鸡后,何克就把我的两个哥哥带回双石铺,成了培黎学校早期的学生。
哥哥去双石铺以后,我和弟弟继续留在妈妈身边。但不久妈妈因病在宝鸡的医院去世,我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一开始,我和弟弟被送到了宝鸡孤儿院。后来,也就是1942年初冬,艾黎把我和弟弟带到双石铺,安置到柏家坪的窑洞里,6岁的我同艾黎、何克的共同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何克和艾黎特意买了一只羊,把产羔后的羊奶给我喝,为我补充营养。他们害怕我寂寞,还买了两只兔子,供我逗着玩,还弄来一只黄狗,天天摇着尾巴陪着我。艾黎、何克晚上回来,常常把我抱在他们的大腿上,给我讲故事,教我学算术,看表上的钟点,教我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因为我太小,还不能在培黎学校上学,他们就送我去上小学。双石铺这个温馨的家,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脑海里储存着许多童年美好的回忆。
在这里,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我享受了两个外国人赋予我的关爱。这种在特殊环境中,汇聚而成的特殊的家,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实,不只是我,当时还有包括我的两个哥哥在内其他60余名战争孤儿,生活在他们所办的培黎学校中。随着战局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不受战争的侵扰,学校于1944年底开始往甘肃山丹县搬迁,1945年春天,学生老师和设备全部搬迁完毕。何克亲自带领学生修建废弃的庙宇,将其改造成为教室、宿舍、实验车间。教学秩序很快恢复正常。他远离故土身居异乡,久别英国亲人,却在中国找到了他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为了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他把家里寄给他的钱都捐助给学校。很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向他袭来,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他在1945年7月22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艾黎守候在他的身边。他要来笔和纸,写下了“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那时何克年仅30岁。
艾黎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何克临死前要求我照看这几个孩子,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老大和老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两个小的———老三和老四一直跟我住在擂台,直到解放。”何克逝世后,艾黎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山丹办学上。他不仅要设法搞办学经费,增添教学设备,聘请中外教师,还要亲自教学上课,教授英文、机械原理、农机运用等,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的饮食起居,包括给我的弟弟晾晒尿床后的被褥。他可够辛苦的了!学校搬到山丹后,我们身边还多了几位小伙伴。除了我和弟弟外,还有张维善、房元德。报刊上常见的艾黎同四个孩子,就是我们这四个人。艾黎疼爱我们,但从不娇惯我们。扫地,烧炕,都是我们必须动手做的事情。除了上文化课以外,每人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实习组劳动。我去了纺织组后到机械组,弟弟去织袜组,纽扣组。这样每人至少要学会两样技术。
谆谆教诲“回去后不要当少爷”
解放后,失散多年的父亲通过组织找到了我们,要求我们回东北,艾黎只好忍痛割爱,送我们回老家团圆。在北京,艾黎亲自到当时的前门火车站,送我们回老家。车就要开了,还舍不得离去。临别既不是拥抱,也不是握手,他拍了我一把,语重心长地说:“回去后,不要当少爷!”眼里充满泪水。至今,好几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依旧是那么清晰,我记住了他的临别赠言。我理解,革命胜利了,昔日的孤儿,一下子变成了“干部子弟”,在众人面前,似乎与众不同,表现出干部家庭的优越感,这样,弄不好就会在长大成人后,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这是他极其厌恶,极为担心的事。
我们聂家兄弟四人回到东北以后,艾黎不得不忍受失去我们的寂寞和痛苦。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二哥和四弟后来都在北京工作,在艾黎晚年的时候,我的哥哥和弟弟在周末,常常带着孩子去看望他,使他享受到老年人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弟弟还被破格批准,照顾他的起居,天天下班后,陪伴在他的身边。
艾黎、何克都是平凡的人。何克在中国亲身参加了八年抗战,把他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争取民族生存的中华民族;艾黎,在中国生活、工作了60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被誉为“中国的新西兰人”。他们远隔重洋来到中国,不为个人的功名利禄,在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定位了人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他们应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和纪念。(供稿:甘肃省山丹艾黎纪念馆作者:聂广涛编辑:刘蓉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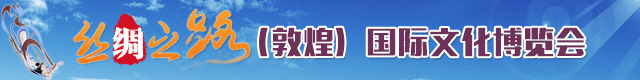



 “活力新区”摄影大赛入选作品
“活力新区”摄影大赛入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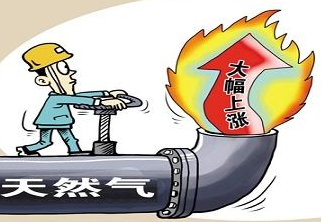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这5年,习近平向世界展示“中国名片”
这5年,习近平向世界展示“中国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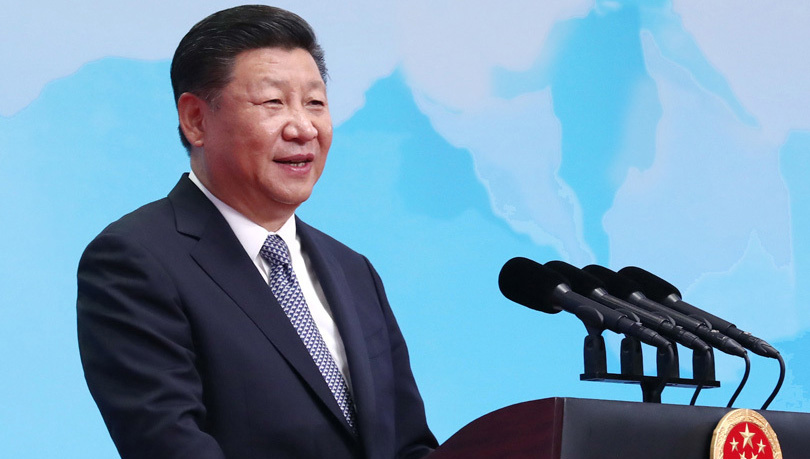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郎朗钢琴广场建成 揭幕仪式上压轴演出
郎朗钢琴广场建成 揭幕仪式上压轴演出
 《战狼2》逼近50亿 吴京:成绩归零 学习不被资本绑架
《战狼2》逼近50亿 吴京:成绩归零 学习不被资本绑架
 你都不知道的微信
你都不知道的微信
 刷爆朋友圈的聚会
刷爆朋友圈的聚会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新闻快报 金昌市举行“大爱金昌 情暖花城”慈善募捐活动
新闻快报 金昌市举行“大爱金昌 情暖花城”慈善募捐活动
 新闻快报 “富民兴陇”系列讲座2017年第9讲举行
新闻快报 “富民兴陇”系列讲座2017年第9讲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