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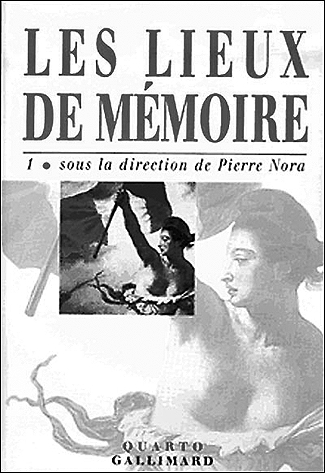
《记忆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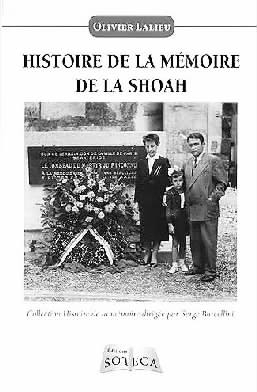
《大屠杀记忆史》

拿破仑战争场景图
法国记忆史研究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30年而方兴未艾。在此期间,各种专题性或综合性的记忆研究文丛纷至沓来,如“刻录记忆”“历史、记忆与遗产”“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历史”“历史与战士的记忆”“重要战役与各民族记忆”以及新近推出的“记忆史”等大量系列丛书,仅“刻录记忆”丛书到目前为止就已出版了563种图书,内容涵盖各个学科领域,历史学在其中占据着十分显赫的位置。各种学术会议也层出不穷,主题涉及记忆史的各个重要研究领域:殖民和非殖民化历史、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遗产、维希政府和犹太人的命运等,如2012年10月在巴黎举办的“作家论坛”,研讨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进程塑造的多样记忆;2013年11月巴黎军事博物馆主办的“从记忆到历史”国际研讨会,以老兵回忆为基础探讨20世纪的创伤性话题——老兵问题的研究状况和路径,诸如此类的会议不胜枚举。
法国这股史学新潮流兴起的动力,源自二战后法国社会政治和集体心态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战后工业化的有力推动下,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农业人口急剧下降,代之以深度的城市化,所谓“深邃的法兰西”的农耕社会观念渐行渐远;对民主共和体制的共识已然生成,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分歧和冲突不再是扰动法兰西民族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非殖民化和全球政治成为法国人界定自身政治价值信仰的标杆。对于在历史时空中逐渐消逝的“我们失去的世界”,一种集体的历史乡愁弥漫开来,正如《记忆的场所》主编皮埃尔·诺拉所说:“人们之所以如此之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它不再存在。”在此种背景下,作为出版编辑兼历史学家的诺拉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酝酿出版一套有关民族记忆场所丛书,意在“将维护和保持社会恒久长存所需要的想象力激发出来”,同时革新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通过他的精心组织、协调和亲身参与,第一部分《共和国》1984年面世,旋即在欧美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两年后第二部分《民族》出版;1992年又推出第三部分《法兰西》,最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记忆场所系列。
《记忆的场所》的面世,是法国记忆史研究当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不仅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表现法兰西的文化特性,帮助锻造民族身份认同,而且使民族历史得以体现的各种物事——包括纪念碑、博物馆、历史文本、人物、城市等实在的、象征性的或功能性的场所,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对激发法国记忆史研究的热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籍出版的第二年,词组“记忆的场所”即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成为与民族集体记忆对话交流的中心词语。而且,它开辟的新视野和新路径,使其影响迅速扩散到欧美乃至亚洲各国,作为样板被应用于研究各种不同的记忆文化,2015年底中文节译本出版。
诺拉原本计划将构成民族的元素拆解开来,一个个单独加以研究,在重视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以象征性语汇重新诠释法国史。他希图通过这样的视角,开辟一条通往新型史学之路。这种史学对结果的兴趣甚于对原因的兴趣,对事件构建过程的兴趣甚于对事件本身的兴趣,对事件不断地被再利用或误用的兴趣甚于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兴趣,对传统构建和消失方式的兴趣甚于对传统的兴趣……其目的在于反抗线性的历史叙事,解构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反映多样的声音。
然而,他最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幽灵”。众多评论者集中批评的一点是,《记忆的场所》原欲做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解构者,但最终却无意中重构了一部整体的法兰西史,展现的更多是中央集权的雅各宾主义法国图景,并成为一座纪念的丰碑。之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盖因两种智识因素的辐辏:一是抽象层面上,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氛围中浸润着深深的民族—国家关怀,正如沈坚教授指出的,诺拉是在法国社会和文化心理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境下,试图拯救民族记忆,重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具体操作上,诺拉在记忆的界定上,深受法国历史学家哈布瓦赫的影响,即有多少个族群就有多少种记忆,但每个族群都有自己一以贯之的记忆语言。这样的定义必然导致对法兰西民族内部异质性的排斥,更多地强调同质的一面以彰显它作为一个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这种内蕴在方法论中的排斥机制,使《记忆的场所》将法兰西民族特性局限在晚近才形成的六边形领土之内,既未能完整地呈现形塑法国民族特性的历史图景,也未能准确地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实图景。其一,漫长的殖民历史、残酷的非殖民化冲击以及后殖民时代移民缺席,但它们曾是法国历史的重要一页,其影响延续至今(尤其是移民问题);其二,忽略了法国内部多样且相互冲突的地区差异和阶级分层,民族—国家层面的集体记忆压倒了复杂多样的地方性记忆共同体;其三,那些与民主共和价值相悖的历史也未得到应有的关照,譬如拿破仑帝国和维希政权。
但无论如何,《记忆的场所》在法国乃至世界记忆史研究中的开创和引领之功是无可否认的。而且,就法国来说,它的遗缺实际上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开拓的空间。近年来,法国记忆史论著源源不断地出版,蔚为大观,主要聚焦于殖民史和战争史领域,在研究对象上趋于注重地方和群体/个人的记忆,而非六边形之内的法国民族—国家记忆。
首先,在殖民史方面,阿尔及利亚、西非、圭亚那、加拿大和黎巴嫩等法国不同时期的殖民地均有专门的著作涉猎。阿尔及利亚是殖民记忆史研究中最为醒目的热点,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至今尚未愈合的巨大创伤事件,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残酷战争和后殖民时代双方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之成为法阿两国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记忆之所。2014年出版的《我父亲,一位老兵的人生旅程》是一部私人史,作者米歇尔·梅萨埃尔历时五年搜集证人证据,回顾其父和家庭颠沛流离的历程,揭示了战争给普通人命运造成的影响。本杰明·斯托拉教授所著的《面向所有人解释阿尔及利亚战争》(2012),在缕述了战争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之后,转而通过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战争老兵、侨民和移民等不同群体的战争记忆,勾勒这场战争给法阿双方留下的政治后果和记忆遗产。他希图借记忆的复原实现身份构建,消弭偏见和双方持久的怨恨。此外,2015年普罗旺斯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一本题为《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一部断裂史》,除回顾1830-1962年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艰难处境和身份转变外,末尾也提到了这种经历给他们留下的种种记忆的场所。
其次,战争主题的论著是许多记忆史文丛重要的组成部分。大至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小至知名或不知名的单个战役,均被纳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仍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法国人的记忆中,且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因此成为记忆史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史学家们梳理了二战中“抵抗运动与通敌合作”这对相互冲突的记忆在当代法国的演变过程:战后初期为重构国民团结和民族共识而制造的“抵抗主义神话”;1947-1968年的记忆爆炸和戴高乐派记忆取得胜利;1969年之后抵抗主义神话终结,对维希政权时期的看法变得更加精细。“集中营和大屠杀”的记忆也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945-1961年被遗忘的大屠杀;1961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犹太人记忆得到彰显;20世纪80年代初犹太人记忆的胜利。尽管不像美国那样,大屠杀在记忆史研究中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地位,但法国对该主题的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与记忆之间”丛书中包含着大量相关著作,“记忆史”丛书2015年推出的两部著作中就有一本题为《大屠杀记忆史》。
总的说来,法国记忆史历经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间的种种发展变化,是学术自身创新发展需求的结果,也与思想氛围转变紧密相关。身处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记录过往的记忆,既是我们对先辈的责任,也是我们自己安身立命的支柱,对于正急剧从千年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甘肃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
甘肃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
 乡村记忆博物馆留住“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博物馆留住“乡村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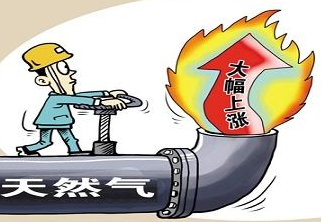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灵台县天然气公司乱收费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盘点那些曾经感动中国的军人
盘点那些曾经感动中国的军人
 绮丽光影点亮日本古都奈良之夜 梦幻唯美(组图)
绮丽光影点亮日本古都奈良之夜 梦幻唯美(组图)
 莫文蔚期待与李宗盛再合作 因缘分献声《美人鱼》
莫文蔚期待与李宗盛再合作 因缘分献声《美人鱼》
 小李子"夺奥路"敌影重重 万磁王、德普船长都是劲敌
小李子"夺奥路"敌影重重 万磁王、德普船长都是劲敌
 女与继母争房产
女与继母争房产
 房车营地
房车营地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刘伟平在审议“两高”报告时说 报告充分体现坚持党的领导 正确政治方向和司法为民理念
刘伟平在审议“两高”报告时说 报告充分体现坚持党的领导 正确政治方向和司法为民理念
 欧阳坚在临洮县调研时强调 从严从细从实做好建档立卡基础工作
欧阳坚在临洮县调研时强调 从严从细从实做好建档立卡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