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绚丽甘肃】大堡子山一场劫难揭开秦公大墓身世
特约撰稿人 孟子为
礼县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人类早期的文明活动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早在7000年前,这里诞生了灿烂的仰韶文化;4000年前,寺洼文化和仰韶文化在这里交融。在这一带行走,就像走进了历史长廊,处处可以看到或听到久远的风物和故事。然而二十世纪末,礼县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国家级贫困县却因一场盗墓风潮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国中“声名鹊起”。短短几年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洗劫一空,无数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

秦公簋(guǐ)
触目惊心的古墓浩劫
据有关文字记述,盗墓活动始于挖掘“龙骨”,所谓“龙骨”,其实是大型的古生物化石。上世纪80年代末,礼县部分乡村的农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四处寻找、偷偷摸摸地开始了挖掘“龙骨”的地下活动,将其作为名贵中药材出售,换取钱财。
挖掘龙骨很快成为一时风潮,由礼县波及邻近的天水市、西和县的数十个乡镇,蔓延西汉水流域一百余公里及其主要支流。期间不断传出有人在挖龙骨时挖到古墓、得到宝藏的消息。这些消息像风一样飞快地弥散各地,一些不法贩子闻讯而动,赶赴礼县。他们最初以低廉的价格搜罗流散在农民手里的零星古董,继而以越涨越高的现金坐地收购出土文物。
一场肇始于“先富起来”的脱贫梦,演变为部分村庄大规模的盗掘古墓,而且来势迅猛,极为罕见。“若要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顺口溜,也成了当时礼县最为流行的语言。
龙骨,很快就被人置之脑后,再也没有人指望它发家致富了。
渐渐地,盗墓的中心地址集中到了礼县永兴乡的大堡子山上。大堡子山位于西汉河北岸,像依山伸出的一只巨大拳头,堵塞了通往礼县的道路。1949年后,为了通行便利,当地政府炸开岩石,修筑了一条盘山公路。疯狂盗掘古墓的野火,最终“包剿”了大堡子山。这座尘封了2800年的秦先祖陵园,遭遇了一场千古浩劫,大堡子山变成了满目疮痍的狼藉之地。
1993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当时《甘肃日报》驻陇南地区记者祁波采写的报道《古墓悲歌》,报道了礼县盗墓的消息。《甘肃日报》也发表了《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省、市、县三级文物单位深感事态紧急,接二连三地召开文物保护会议。多管齐下的结果,使礼县的盗墓活动基本得以遏制,截获和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现在,收藏于礼县博物馆的许多文物,就是当年亡羊补牢的收获。
1994年3月,料峭的春寒还未散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大堡子山,对被盗掘的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戴春阳在回忆文字中写道:由于对此墓地的盗掘系从墓地的东北、北部开始,直至蔓延到墓地的中心区域、故盗洞均按墓地中小墓的5-7米挖一个盗洞,墓地中心区域亦以此密度盗挖,虽更多的盗洞或与中心区的大墓相去甚远或挖至大墓的边缘或墓道,但当恰挖至墓室又恰侥幸挖至置放随葬品的位置得到文物后,其他盗墓犯罪分子即蜂拥而至疯狂劫掠。盗墓犯罪分子甚至在大件随葬器物盗出后,还将洞内的墓葬填土均用手细细的搓滤,以盗寻小件文物。正是这种经年累月的从容盗掘,致使墓地中心区大墓和车马坑内珍贵文物洗劫一空。

秦公鼎
秦公大墓的历史谜团
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在陕西出土。这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地下军团”,以其举世罕见的阵容轰动了世界,也推进了秦史的深度研究。众多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秦人有四大陵园区。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二、三、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临潼秦始皇陵园,先后在陕西发现,唯有秦人的第一陵园一直难觅踪影。学术界处于历史研究,地方政府处于开发旅游业的需要,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寻访,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史记·秦本记》记载,秦的祖先最初居住在“西犬丘”,因牧马有功,且在与西戎的战争中视死如归,所向披靡,被西周王朝封地授侯,得以建立秦国。“西犬丘”实际上是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和根基所在。
《史记》之后的史书,所记载的“犬丘”有两个。一个在今天的陕西省,一个在今甘肃省。确定“西犬丘”的准确位置,是解开秦人第一陵园在何处的关键。
1919年,甘肃礼县红河乡出土的青铜器——秦公簋曾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广泛关注。这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宝,是先秦著名的青铜器,上有铭文105个。1849年,这只秦公簋几经周折传至北京,著名学者王国维、郭沫若等人撰文考证,认定秦公簋是秦肇始文明的最重要实物证据之一。
王国维和郭沫若等大师难以预料的是,上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的被盗和发掘,意外地证明了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西犬丘,就在甘肃礼县。这里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重要都邑,是秦先祖、秦早期文化的发祥地,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祖先的“老家”。礼县被盗掘的秦公大墓,就是秦人的第一陵区——西垂陵区。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坪乡和永兴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隔河与南岸的山坪城址相对,西侧有永坪河自北而南注入西汉水。西汉水以东的河谷平坦开阔,一马平川;以西则山势险峻,狭窄蜿蜒。墓葬遗址西面、南面石壁陡峭、不可攀登,东面较缓,北面与起伏的群山相连接,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从地理位置上看,大堡子山“两河夹一山”的独特地势,完全符合先秦贵族选择陵园的“风水”取向。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重点调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新发现的数十处早期秦文化遗址。
2006年9月初,联合考古队进驻大堡子山,发掘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联合考古队在礼县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墓葬400多座以及零散分布的文化堆积层,足以证明礼县文化遗存丰富,还有许多历史的真相深埋在地下。在被盗秦公大墓的西南角,联合考课题组古队发掘出了一处建筑遗址。从地层堆积和夯土内的包含物看,这个建筑规模宏大,大约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初,战国时期废弃,汉代遭到严重破坏。近代因修整梯地,东墙地上部分完全被毁。专家认定,这个建筑应是秦人的大型府库类建筑。联合考古队又在被盗秦公大墓西南20余米处发掘出了一个祭祀遗迹,4座人祭坑、6个灰坑和1座乐器坑。人祭坑里有一具年龄约为35岁的女性尸骨和一具中年男性尸骨,还有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专家认为,这种用人来当作祭祀的祭品,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非常符合秦朝时期的历史特征。
原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先秦史学者祝中熹先生认为,秦人第一陵区的范围,原来都是在陕西关中一带寻找。西垂陵区发现之后,才算是找到了秦人最早的一处国君陵墓。西垂陵区的发现,不仅在时间上,也是在地域上,填补了秦人历史的一段空白。
在一座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乐器坑内,南北两侧排列着乐器。南侧为铜钟镈与钟架,北侧为石磬与磬架。属于春秋早期3个铜镈和8个甬钟,在坑道里一字排开,外观完整,锈色深绿,纹饰华贵,一出土就成为这次发掘中最引人瞩目的亮点。铜钟镈由西向东、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在3件镈上或一侧发现3件铜虎。镈、钟上附有铜挂钟,置放在镈、钟之上或一侧。镈和甬钟的表面还有残留的布纹。
在20世纪末期礼县的古墓浩劫中,这些国宝与盗贼擦肩而过,侥幸留存,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在钟架的一侧,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石磬,共10件,按照由东向西、由大到小的方式排列。石磬的上方是磬架,这组石磬很有可能就直接悬挂在磬架。出土的编钟保存非常完好,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做了编钟奏乐演示,编钟发出音的响清脆悦耳,美妙动听。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朱东生教授说:“秦公大墓出土的这11件铜钟镈乐器,音域、石磬宽到3个多8度,铜钟镈的音色和音质、音准都非常好,可以演奏很多器乐。古人对器乐的排列,是按宫商角徵羽编造的。用现在的简谱表示,就是哆来咪嗦啦这五个音组成的。用这五个音,就可以演奏很多乐曲。”过去,一些研究秦国音乐史的专家认为,秦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只有17年,秦国的音乐不可能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达到某种高度。这次出土的钟镈和石磬,证明在春秋时期,秦国宫廷里钟磬齐鸣,乐队气魄宏伟,秦人的音乐风格已经成型。
礼县出土的青铜诸器上,多数自铭“秦公”:秦公簋、秦公壶、秦公鼎。但因为墓葬中文物的大量流失,考古工作者始终无法确认这座秦公大墓的主人。
《史记》记载,秦国有两位国君葬于西垂。他们分别是秦襄公、秦文公。目前考古学和历史学专家已一致确认:大堡子山古墓就是秦公墓,其墓主可能是庄公、襄公或文公。
有人认为,礼县大堡子山墓地二号墓的墓主是秦襄公,三号墓的主人是襄公夫人。其论据主要是,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有浓郁的西周晚期风格,存在着和秦文公所处的时代有着时间上的差异。“秦公”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还不能确定。
近年来,海内外已经发现了多件署名“秦子”的器物,其中的大部分出自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的秦公大墓。学者们认为,有“秦子”铭文的器物,属于春秋早期。但笼统的“春秋早期”,时间跨度最少也有三四十年。在君位更换比较频繁的情况下,秦子可能不止一个。“秦公”没有确定,又出现了“秦子”成为难题。这就是秦西垂陵区发现后给学术带来的诸多难题的一个缩影。
原甘肃省博物馆原历史考古部主任、秦史学者祝中熹说:“大堡子山发现的两个大墓,按照《史记》的记载,埋葬在西垂陵区的还有秦庄公。再往前推,秦先祖非子之前,还有大骆,包括大骆内,非子以前的秦国国君都生活在西北地区,他们的墓葬到底在何处?例如,秦国的国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垂、西犬丘,到底在什么地方?陵区在大堡子山,秦人的国都离大堡子山不远,但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秦西垂陵区出给学术界的所有难题可以归结在一个核心问题上,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现在礼县大堡子山的疯狂盗墓事件。




 庆阳蒲河川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庆阳蒲河川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天水麦积山2016年冰雪旅游启动
天水麦积山2016年冰雪旅游启动








 甘肃康乐县如此贫困的一家人
甘肃康乐县如此贫困的一家人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云南城投兰州野蛮拆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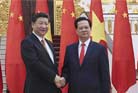 习近平会见越南总理阮晋勇
习近平会见越南总理阮晋勇
 李克强会见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
李克强会见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
 赵薇靠幕后交易赚2亿? 否认:新闻纯属虚假(图)
赵薇靠幕后交易赚2亿? 否认:新闻纯属虚假(图)
 杨幂:绝不带小糯米录节目 给她被保护的童年
杨幂:绝不带小糯米录节目 给她被保护的童年
 兰州超市做到了吗
兰州超市做到了吗
 火车票黄牛消失
火车票黄牛消失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我省今年年内有4条铁路线投入运营更多出行选择!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大批天鹅到甘肃高台黑河湿地越冬画面壮观艳丽
 电影《柴生芳》观影及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连辑出席
电影《柴生芳》观影及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连辑出席
 精准扶贫的甘肃模式 危房改造:修了群众房 暖了百姓心
精准扶贫的甘肃模式 危房改造:修了群众房 暖了百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