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丨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一首长诗的来龙去脉
原标题:名家访谈
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一首长诗的来龙去脉 1

人物简介 牛庆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甘肃日报文艺部主任、高级编辑。出版诗集多部,获多项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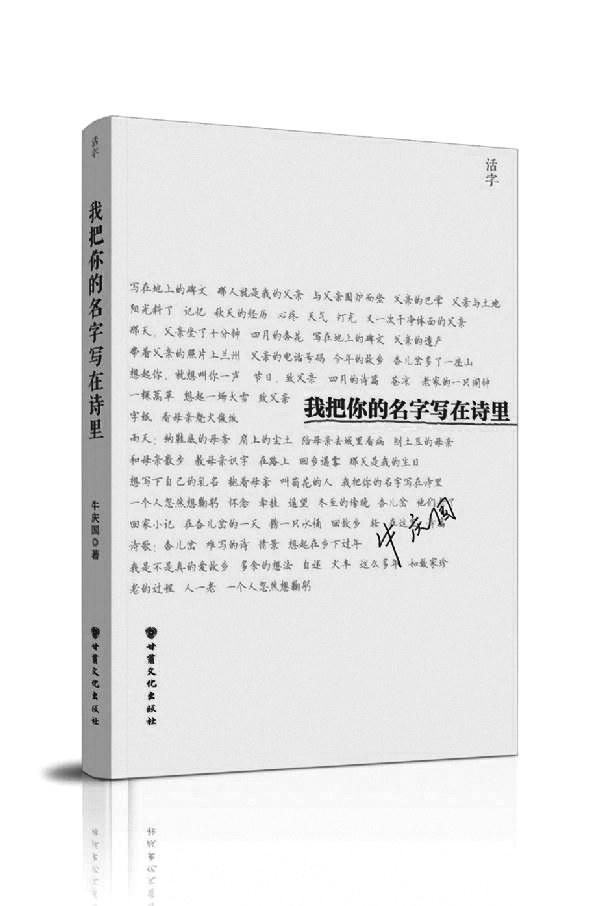

杏儿岔8号
四月的兰州,到处可以看到锦簇绽放的花,其中一定有杏花。在甘肃会宁一个叫杏儿岔的地方,那里的杏花也应该早就开了。杏儿岔是一个小到在地图上难以搜索到的村庄,却因为牛庆国的诗歌,在文学的版图上声名远播。牛庆国写过杏儿岔,写过杏花,写过四月的杏花,最近又写了一首长诗,叫作《祖河传》。这首诗,写祖厉河,却比祖厉河深广;写故乡,却比故乡辽阔。
从杏儿岔8号到白银路123号
祖厉河是会宁境内一条有名的河,是牛庆国故乡的河。
祖河和厉河,在会宁东边发源的叫祖河,在南边发源的叫厉河,两河在会宁县城汇合,合称祖厉河,向北流入黄河。其实在杏儿岔村口还有条小河,在当地村人的记忆中,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一条“能苦死蛤蟆”的小河,也是祖厉河的一条支流。
从杏儿岔8号到白银路123号,牛庆国走过了很远的路。前者是他血缘上的老家,后者是他工作的地方,也是他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
牛庆国还在会宁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来兰州见到黄河,他不禁发出感叹:“那一刻,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河、这么多的水,从所未见!”后来,他长久地定居在黄河之畔的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写作,父母在老家相继故去,他和大多数子女一样为老人送终。为了表达对亲人的感恩、疼痛和愧疚,他出了一本诗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诗里》。这部本来很私人化的诗集,出版后却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和《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诗里》不同,《祖河传》更多趋向“公共书写”的属性,这也是这首长诗取名“祖河”而非“祖厉河”的原因之一。祖河,就是祖先河,是流在时间里的河,是许许多多的河。
牛庆国写长诗《祖河传》,是一次出差坐火车从河西回到兰州的途中动意的。早年他在《火车》这首诗中写过“在火车时刻表的缝隙中/想起这些年走过的路/现在一条条布满我的身体”。火车旅途中的冥想,容易让人坠入时间的河。
时间流经的河,也是人走过的路。在长诗《祖河传》中,“我”和“我们”沿着河流的指引,扶老携幼,风雪兼程,从孤弱走向壮大,从逼仄走向广阔,从过去走到现在。
阅读牛庆国的诗歌,会给人以踏实感。早年农村盖房子,都要提前打好土坯。那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劳作,一锨一锨将半湿的土放进一只长方形的木制模具里,用脚踩实,再用石头的“础子”一下接一下砸实,取出后一层一层码起来,等风干后用来砌墙。在牛庆国那里,一首诗歌的完成类似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字撑起一个词,一个词撑起一句话,就这样逐字逐句、稳扎稳打“夯实”一首诗。《祖河传》写写改改历经三稿,第二稿与第三稿之间时间跨度近两年。创作完成后,首发在《飞天》2021年第二期。就像通常审校报纸副刊上的文章那样,尽管《祖河传》已经发表,他还是在样刊上用笔勾画修改了好几处。显然,他对这首诗很看重。
牛庆国说,《祖河传》是他诗歌写作的一座分水岭。无论从风格还是体量上来看,都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这首诗中,尽管依然有村庄、苦苦菜和苜蓿等从审美惯性来看属于“乡土”的意象,但已经超越了乡土范畴,就好比一滴水流淌在具体的祖厉河里或许是乡土的,而在抽象的时间河流里,它越出乡土的河床,具备了历史感和时代感。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读者看完《祖河传》后,觉得这首诗是写给建党百年的红色诗篇。牛庆国认为,诗歌也是记录,自己作为会宁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大的人,亲历见证了在党的带领下父老乡亲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必然会将这种认知和体验带入诗歌写作中。《祖河传》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正如诗的结尾写的:“现在/我们要把河带向远方/我听见河水/答应了我们”。基于读者和诗人之间的约定,读者也会把一首诗带向远方,在不断阅读中不断完成。
牛庆国:《祖河传》是我写作风格的转变之作
3月29日,针对《祖河传》这首长诗的来龙去脉及其创作,牛庆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你是在什么情形下开始创作这首长诗的?
牛庆国:有一次出差途中,从河西往兰州的车上,想起以一条河流隐喻的方式来写一写家族的历史和故乡的传记。但真正动笔写作的时候,发现自己写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一个地方、一条河流,而是漫向时间深处。前段有位老同志看到这首诗后跟我说,他正在修家谱,想把这首诗收录进去。家谱毕竟是很私人化的,对这个提议我未置可否。说这个例子,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首诗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记者:看这首诗末尾标注的一二三稿的时间,从创作到完成历时整整两年。修改前后的变化大吗?
牛庆国:《祖河传》发表出来后在280行左右,但起初体量比这要庞大。从写家族史开始,第一稿写了五六百行,把家族具体的人和事写得比较多,在第二稿修改时删了好多;等到修改第三稿的时候,把过于个人化的内容又删掉了好多,尽管有些心疼,还是咬牙删掉了。前前后后修改期间,有时因为工作,有时忙于生活琐事,就停下来,放一放,改不到称心如意的时候,不去硬改,这也是我一向的写作习惯。
记者:这首诗与以往创作有何不同?
牛庆国:这些年随着家里老人的去世,我在城里生活时间也长了,加之脱贫攻坚以来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人在认知、体验上更深了一层,面对新的乡土社会,写作者也需要新的表达。《祖河传》本质上还是立足农村,还是以农村的人和事为主,但不同以往作品,不是面向具体的某个村庄,而是比较宏大的题材,甚至有民族的、时代的、历史的思考,手法上也有变化,算是对过去写作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我写作风格的转变之作。
记者:这次转变,是否在刻意突破?
牛庆国:一个写作者,可能在某一时段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表达方式或风格,随着自身积累的加深,必然会有转变。我们时常听人教导年轻人写作要突破、要转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必急于求成的过程。这就像生孩子或孵小鸡,如果一味过早突破、求变求新,就容易早产,后果就是作品不成熟。
记者:《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诗里》那本诗集感动了许多读者,曾引发“感人”是否是诗歌评价尺度的讨论。相较而言,《祖河传》偏向“理性”。你怎么看?
牛庆国:《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诗里》是我的一本诗集,也是诗集中的一首诗。那首诗里有大量的细节,是写实的、具象的,而《祖河传》虽然也提到了父辈、故乡,但是超越了个体的父母和故乡,而是历史的、时代的父母和故乡,可以说是浓缩了很多的“父母”。在《祖河传》的一些表达中,我甚至回避了“父亲”一词,而是用到了“头人”。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祖河传》在艺术上超过《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诗里》,或许这也是一种偏爱。
关于感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打动人和感染人是衡量艺术作品
优劣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艺术作品的功能就在于记录、启发、感染、教化,如果连感人都达不到,文学的功能和效果就打了折扣。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观点,有人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被大多数人读懂,是自己的耻辱”。我个人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尽管文学创作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风格,但如果一个作品让人读不懂、读后不感人,是拒绝读者的,某种意义上是未完成艺术使命,也是失败的作品。
记者:你介意“乡土诗人”这一标签吗?
牛庆国:从文学批评研究的角度这样界定,或许是为了方便,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作家、诗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写同一种题材,不管写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在讲述时代,表达的是一个写作者对生命的深层体验,好比我们的身体对疼痛的感知都是一样的,并不分农村和城市。
记者:诗歌创作在你的生活工作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牛庆国:如果给工作、生活、写作排序的话,在我这里,写作通常不占第一的位置,往往是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事。我们首先是一个家庭成员、工作人员,活生生的正常人,就不能放弃现实的社会责任。我不太赞成写作者尤其是青年写作者模仿“名人轶事”中的桥段而去放弃正常生活专门成为一个“文艺青年”的行为,鼓励他们这样去做,从世俗角度来说这是不负责任的。
祖河传(节选)
一
我加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有几个人
每个人走的路程不一样
但他们那时走在一起
那天黄沙蔽日诸神奔走
在一座破败的庙前
他们找到了一条河的源头
他们的欢呼和野兽的悲鸣
交集在一起
那天母亲躺在干净的黄土上
我听见她的血渗入黄土的声音
像一家人在悄声议论着什么
她微笑着
但满脸都是泪水
那天天地没有任何预兆
我无法知道自己的前途
母亲只将一把将熟未熟的扁豆
揣在我的怀里
我就跟在了他们后面
但我忘记了那是哪年哪月的哪一天
二
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个童养媳有一个富家小姐
还有一个被剪过辫子的男人和一个曾经走南闯北的脚户那时一条河的声音
就是我们的喘息
我们一直沿着河走
像一队雨前奔走的蚂蚁
我们遭遇了烈日暴雨风雪
也遇上了巫师鬼魅神灵
有的坎过了几次才算过去
有的路走了好长时间才走过去
我们比时间走得更慢
文/记者 张海龙 图/受访者提供
相关新闻
- 2021-04-01甘肃文化丨奇特的镇墓兽
- 2021-04-01揭秘:“关照”一词出自甘肃嘉峪关
- 2021-04-01村落名中藏着甘肃州县名 这些你还不甚了解的“敦煌故事”
- 2021-04-01历史眼丨兰州市博物馆大门 大有来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