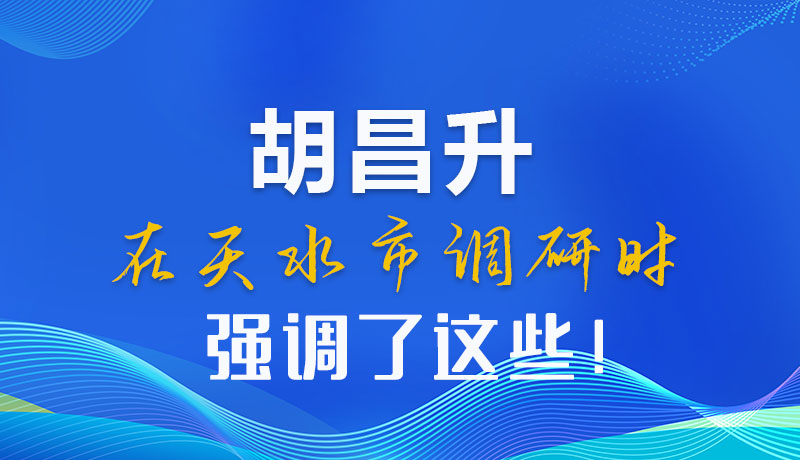井眼里的时光
三眼井遗址在景泰县上沙沃镇境内,距县城一条山镇约20公里,原名“汜水关”,因井内有三个泉眼同时出水而得名。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曾是五世达赖喇嘛讲经的地方,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站在三眼井村外的土坡上,忽然听见了驼铃。那声音像是从地底渗出来的,混着砂砾摩擦的沙沙声,在十月的风里忽远忽近。村口的沙枣树簌簌摇动枯枝,折断的夯土墙被夕阳拉出细长的影子,仿佛当年的商队投在戈壁上的轮廓。
三眼井堡建于明代,具体时间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兵备副使荆州俊修建。遗址原为汜水关,是鞑靼东西往来的重要通道。遗址四面环山,地处褶皱地带的沟谷地段,城址东西200米,南北150米,四角有角墩,北墙正中有敌台,城门位于东北角,门宽7米。城墙为黄土夯筑,城周有护城河,东西240米,南北约180米。城内有古井遗址一处。东面紧贴城墙有一利用自然山包砌筑的一个平台(西、北、南三面以块石砌垒,中填土夯筑而成),平台上原有楼阁,现已全部被毁。城南砂河地面有教场遗址一处。城墙为黄土夯筑,城周有护城河。
古井依然在废墟里沉寂着。或许是少有人迹的缘故,井水上漂浮着一层枯叶,但外溢的流水清冽,在坍塌的角墩与断墙间蜿蜒成溪。四百年前的戍卒是否也在此汲水?或许某个清晨,他们刚放下木桶,便望见地平线腾起的狼烟。万历二十七年的夯土层里还嵌着麦秸,荆州俊督建关城时,是否料到这座西北雄关终将沦为牧羊人的临时居所?
现在的三眼井堡遗址内的村民已全部搬迁,仅有两户牧羊人临时居住。遗址是一片废墟,残垣断壁,满目萧然。遗址内的古建筑和历史遗迹虽然破败,但仍能感受到其昔日的辉煌和历史沉淀。
踩着龟裂的护城河底行走。这条曾令鞑靼骑兵却步的深壕,如今蜷缩成浅浅的沟壑,几簇骆驼刺在沟底开出细碎的黄花。北墙敌台只剩半截土墩,青苔爬满石砌的基座,像是给残破的铠甲缀上了绿松石。手指抚过城墙断面,夯土里交叠的纹路如同史书褶皱的册页——十四厘米的夯层里藏着多少戍卒的号子,十六厘米的间隙中又漏掉了多少场春雨?
牧民们至今传说,过去有高僧诵经时井水漫过石沿,在教场遗址汇成镜湖,倒映出雪山与经幡。而今只有蜥蜴在晒得滚烫的教场石板上疾走,带起细小的沙尘。
城东石砌平台残留着楼阁的幻影。块石缝隙里,几株沙冬青把根系扎进明代填土。据说这里原是守将观敌的哨楼,我们却总觉得该有文人墨客在此凭栏——或许某个中秋,来自长安的商贾在此望月,将碎银般的月光和着井水酿成乡愁。现在连最顽固的墙基都在流沙中软化轮廓,像浸了水的旧宣纸,渐渐洇开历史的墨迹。
暮色漫过城墙时,将几百年的月光、驼铃、诵经声和烽火,都化作水面细密的涟漪。放羊人赶着云朵般的羊群归来,咩咩声惊起废墟间的夜枭。它扑棱棱飞过残缺的角墩,翅膀剪开紫灰色的天幕,恍若当年传递文书的信鸽,驮着最后一道晚霞投向苍茫的祁连山。
井台边的湿地上,新生的芦苇正在抽穗。它们柔嫩的茎管里,或许藏着某个戍卒未寄出的家书,某位高僧遗落的偈语,又或者只是明代某个深秋,一片不肯坠落的胡杨叶。
瞿学忠 甘霖 彭维国
- 2025-04-09敦煌“飞天”舞风情 《丝路花雨》在江西盛大上演
- 2025-02-24七律·华夏撼世重抖擞
- 2025-04-08西北民大推出线上课程千年敦煌舞韵触手可及
- 2025-04-08《敦煌舞基础训练》慕课课程上线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