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琴:如豆微光所照及的文学现场
原标题:尚书访
如豆微光所照及的文学现场

张晓琴,1975年生于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客座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著有《直抵存在之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等。获黄河文学奖、甘肃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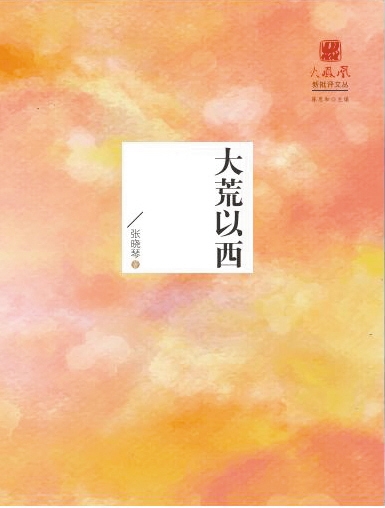
《大荒以西》张晓琴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

《一灯如豆》张晓琴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
张晓琴喜欢猫,家里也养猫,而且养了两只,其中一只是因为亲戚搬家寄养在她家的,她笑称是“人道主义泛滥的后果”,那是一只虎斑猫。张晓琴说这只猫极少与人对视。果然,当人试图套近乎时它警惕地逃开了。就是这样,少有人真正知晓一只猫的内心世界,只不过看到它华美的斑纹。
我们还是要说到文学。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从作家或诗人那里诞生落地,进入传播渠道,被阅读和评价。有的人只看到作品的皮相,比如故事的怪诞、词语的瑰丽,合上书,这本书就从阅读者的眼皮底下逃走了,但有人却能够真诚对视,进入作品内部。通常我们将后者称作是文学评论家,他们是更专业的读者,《大荒以西》与《一灯如豆》两本书的作者张晓琴便是其中之一。
今年年初,《大荒以西》和《一灯如豆》分别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同样是文学评论,但《大荒以西》将批评的视角集中于贾平凹、路遥、陈忠实、杨显惠、于坚、牛庆国等西部作家的作品,倾向于作家诗人的个案研究,《一灯如豆》则面向国内更广阔的文学现场,研究对象有刘震云、刘心武、格非、余华、蒋一谈等作家的小说,而且有一部分是对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命运、非虚构文学、城市文学的形态等文学现象的理论综述性探讨。
张晓琴不止一次看似不经意地说道,“这么多年我发现自己还是挺热爱文学这个行当的。”作为一个70后科班出身的批评家,从本科到博士后,包括在学院所执教的文学专业,她的学术成长路向是如此的有条不紊,从来没有背离文学这一本体。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那就是遇见一首很对胃口的歌往往会选择循环播放,但循环次数多了,发现新鲜感全无,以致后来变得麻木了。有一个网络词汇叫“累觉不爱”。但张晓琴对文学的热爱是彻底的,就像她在作品中多次引用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石头上山的肯定,带有绝望般同情的理解,她在早前的一本书中将类似处境表述为“直抵存在之困”。
直抵存在之困,其实是作家与批评家共同的任务,殊途而同归。长江学者陈晓明教授在《大荒以西》的序言中评价认为,张晓琴“有能力介入复杂的文本,也有能力把简单的文本挖掘出历史与理论的蕴含”。进入一个文本,犹如古人游山探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除了志与力,到了幽暗昏惑之处,还得有灯来照亮。对于批评家,这灯或许不需要作家照亮世界的光芒那般强烈,如豆微光,已经具备纳博科夫“微暗的火”意义上的“给一部晦涩难懂而未完成的杰作添加一系列注释”的严肃功能。
或许,面对物理和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任何文学作品的表达都是间接或未完成的,批评家最大限度地通过合理有效的阐释对其进行衔接与补充。这个过程中,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是在场的持灯者,不仅为了照见作品与世界之间被遮蔽的晦暗地带,也为了自己脚下路径的明晰。对于文学批评精力与锋芒正健的张晓琴而言,“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想必险远可至矣。
张晓琴:今天的文学批评需要一张向西的地图
记者:虽然都是文学评论,但两本书在命名上并没有过于学术化,而是更倾向于文学化。请谈谈两个书名的由来或你的用意。
张晓琴:《大荒以西》一书中的研究内容关乎中国当代西部作家作品,有已经在文坛颇有影响的名家,也有正在成长的新人。身处西部,我的研究目光自然与西部之外的研究者略有不同,就想取一个能够体现西部气质的书名,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句子:“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也想到了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其实是有实有虚吧。
批评很大程度上不止是面对别人的文本,而是从事批评者自我的内心较量。人的心灵事实上就是存在本身,是它所感知的世界的一部分,是一种发光体,它是灯,现代主义的思考如是。灯也是佛教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象,佛教中将彻悟的境界喻为灯被点亮,由此破除黑暗,佛性得以显现。《坛经》有云:“有灯既光,无灯即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盏灯,批评是这盏灯燃烧的方式之一,虽然光亮微弱,却是存在的有力见证。这是《一灯如豆》书名的来由。
记者:正如你说的,《大荒以西》一书集中论述了西部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景观。该如何界定文学意义上的西部?除了书中涉及的作家诗人,进入你批评视域或还未来得及写的还有哪些?
张晓琴:西部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西部的自然环境、民俗信仰、历史人文,都是独特而深厚的,其上生长的文学同样具有独特性。今天的批评需要一张地图,尤其需要一张向西的地图,因为文化意义上的疆域与地理意义上的疆域同样重要。这是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也是我心目中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然而,意识到上述问题后我的批评与写作变得更加艰难,西部过于宏阔,每个作家作品都有具体的文化背景与创作的语境,面对一个作家时的经验在另一个作家那里完全失效,这让我在从事西部批评时既能收获与文本相遇的喜悦,又难免遭遇突如其来的障碍与挫折,而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灵魂的探险。所以,进入我批评视域或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的西部作家作品还有很多。
记者:“文学还活着吗?它还在新媒体中吗?”这是你在《一灯如豆》中提出的一个尖锐诘问。在新媒体时代,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吗?
张晓琴:每一次新媒体的出现,都会给文学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恐慌。然而,只要人活着,文学就不死。人类与语言永远是命运般地融合在一起。只有当人不再成为人,也许他就不需要文学了。人始终想成为人自身,在不断地反省与超越甚至回归。新媒体时代虽然不时传来文学死亡的恐惧之声,但文学依然存在,那些优秀的、打动人的新艺术形式的深处,总有一种文学性在里面,它犹如一个幽灵,存在于它们的内里。
记者:两本书中都有关于作家的访谈录,访谈这种形式如何体现批评?
张晓琴:访谈是一种对话,是思想碰撞的方式之一,它会让问题与思考更加清晰,更加明亮。事实上,阅读与研究也是一种对话,在某种程度上,访谈是阅读与研究的一种有效补充与验证——比如你现在与我的对话。
记者:张定浩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谈论一部文学作品》一文中将“复述”和“引用”作为两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来谈的。这或许是批评者难以回避的两种方法,你在两本书中对此也有颇多运用。可否结合自己的批评实践谈一谈文学批评中复述和引用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张晓琴:定浩是我喜欢的诗人和批评家,也是我的朋友,他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复述主要运用在叙事作品的文学批评中,而引用则是采样性的引文呈现,引向书写者本身,二者有益于更深地理解、接近乃至进入文本,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创造。
记者:最近甘肃举办的一个文艺批评会议上,其中一个焦点是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本的问题,你如何看二者间的关系?用西方文艺理论“套”中国当代作品的解读方式被诟病已久,但另一个事实是论文发表中却要求一定数量的“注释”,如果返身向中国古典文论寻求理论支持又显得不合时宜或捉襟见肘。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晓琴: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解读层面,而是在整个文学批评层面。无论是西方文艺理论还是中国古典文论,作为文学批评的资源时,都应该是“化用”,而不是“套用”,关注点都要向存在的根本靠近,而非炫技式的理论展示。不可否认,我们这一代从事批评的人大都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学院教育与专业训练,西方哲学与文学理论是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理论资源。但面对一些优秀的文本时常常不由联系中国古典的东西,论述时也会运用西方的理论。所以,从根本上看,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或者矛盾的。
记者 张海龙
- 2017-03-31毛生武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学习有关文件精神 讨论研究张掖贯彻落实意见和相关工作
- 2017-03-31兰州市举办“小手拉大手”系列活动——千名小学生演绎文明礼仪
- 2017-03-31兰州市城关区畅家巷学区举行文明礼仪展演活动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











